记忆中的樱:从乡土名字到烂漫花朵,聆听樱花的美好
我宁愿叫你一个字,樱。
简练的字句,清晰易懂。仿佛村寨上空浮游的雾气,农夫从不称其为雾气,仅呼之为雾。如此便不会显得做作。
樱花极为绚烂,有时甚至极为夺目。年少时回想起来,樱这个字,几乎显得很平凡,如同樱桃。但它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给女孩取名字时,人们常常会选用它。
长大后的樱,依然会像在故乡奔跑的少女,既英气又纯真,脸上总是干净清丽。
偏爱樱花,抑或欣赏日本民歌《樱花》更甚?幼时家中没有电视,唯有收音机可听。
春天到了!樱花绽放,清晨时分天空泛红,云霞映照花朵,它们仿佛在微笑。广阔的天空中白云舒卷,那迷人的香气随风四处散播。快去欣赏,快去欣赏,赏花须趁天色尚早。曲调婉转悦耳,从箱中传来,一直沁入心田。
于是,就知道了樱花,并意识到它的好。
后来上大学时看到了樱。在北京的紫竹院公园。
紫竹院在春天里,显得格外清静,也分外雅致。樱花从一簇簇竹子后面钻了出来,一簇一簇,一树一树,粉白交织,显得格外娇嫩,也特别动人,仿佛是梦境中的景象。
远远望去,并不绚丽,却非常喧闹。许多花苞挤在一起,竞相开放,彼此推搡着,显露出些许腼腆,又带着几分活泼。
那一刻,整个北京的春天似乎都融进了这丛樱花里。
樱花,让我初次领略到一种超越岁月的绝美景象。从那时起,我便对它产生了喜爱之情。
后来某个春天,再次见到樱花盛开。向导表示,古汉台所制的樱花点心最为可口。味道十分清雅。
花也能吃吗?就像《红楼梦》里的女子们那样?
童年时曾尝过榆钱,一次能拾掇好多。那滋味甘甜,口感又松软,仿佛微风拂过般轻盈。后来又吃过洋槐花,甜度更高。把它包进饭团里,香气四溢,弥漫很远。
樱花树边的台地上,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石门十三品,也就是《石门颂》。这个作品与褒斜道有关,上面的文字已经模糊不清。当初书写者的本意是为了赞美功德,并不是为了展示书法技巧,然而后来人们还是把它当作汉隶中的顶尖之作来敬仰。
热烈纯真之中,蕴含着洒脱的韵味,仿佛邻近那株已生长数百年的古樱树。岩石的醇厚气息穿过漫长的岁月尘埃呼啸而至,总会在蓦然看见时令人豁然明白。

汉台的樱花,现已凋零满地。无法品尝,只能拾取几片泡入茶中。目光所及,那些飘落的樱瓣,看似轻柔而温软。更带有一份幽静。它隐匿于时光深处,不张扬,伺机而动。仿佛当年的汉王。
满院清香。而它却躲进屋角,似乎在做着退场的准备。
终究,只吃到了核桃酥点。于是,也就寂然。
落樱凋零,庭院阶前月光洒落,绣床边的人儿忧愁地倚靠在熏笼上,神情恍惚,恍惚间仿佛是去年的今天,那份遗憾依旧如故,这是南唐后主李煜词作中极少数提及樱花的篇章,词作的风格与作者本人相似,在凄美哀婉的旋律里,隐约透露出人生失意后的哀伤情绪。
那段话出自汤显祖的《牡丹亭》,说情意不知从何处开始,却一直爱得深沉,每次读到,都让人觉得像是经历了前生后世。
如同朽木上飘零的败叶。主根裸露出来,仿佛遭雷轰过,截成几段。偶有新芽萌发,生机勃勃。却无辉煌可言。或许,一味向前,孑然一身,便成了不可逆转的结局。
李商隐亦描摹过樱花,有“何处悲瑟之筝伴随急促之管,樱花长街垂柳之畔”的句子,然其作品不及他篇。樱花本应孤寂,却夹在“悲瑟之筝”“急促之管”之间,平添了纷扰,喧嚣,减损了清雅,便背离了其自然之趣,沦为情绪的寄托。
樱花颜色深浅不一。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写道,“原本此生此世也迷茫,山河时光徒然感伤,最终我,还是要等你。”像是命中注定一般。
这种情景让我回想起幼年时攀登祖宅土墙的经历,心中充满暖意。黄昏时分,远山笼罩在暮色之中,家家户户升起袅袅炊烟,天地间一片昏黄,那时总能从孤独和沮丧中猛然振作。成年之后,我也常喜欢独自一人,前往更遥远的地方旅行。
乡村的平凡,傍晚的忧伤,街巷的热闹,真挚动人。因此,便认为,人间,便是家。后来,在小镇的河畔再次见到粉色的花朵。
那个时期的樱花,沐浴在春日和煦的阳光里,宛若一个凭窗伫立的淑女,显得那般闲适,又带着几分落寞。微风拂过,会传来若有似无的清香。
这个小镇原本没有樱花树,后来几年里引入了一些,经过培育和生长,不知不觉就形成了樱花园,供过往行人休息。三两年时间,这些樱花树就稳固地生长在这里了。
生长繁茂的樱花,蕴含着丰腴的人间气息,令人忍不住举机捕捉。整个四月,整座城市都弥漫着樱花的芬芳。这景象让人联想到一个字,就是“实”。
这个词的形态,触动心弦。像白娘子思念许仙,似张爱玲眷恋胡兰成,也像卓文君倾慕司马相如。它们都陶醉在质朴的时光景致中,美好得如同绽放的莲花。
四月非常铺张,十分热闹。但樱花却很清雅,独自经历着花开花谢。我站在一棵樱树下,花瓣已经凋谢,只看见满树的绿叶。
伸出去的手指间,有春阳漏过,不喜,也不悲。
但安静。一如此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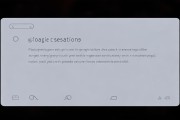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