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低生育陷阱:社会结构与经济走势如何影响生育率
北京晚报 | 作者 叶克飞

《低生育陷阱:日本少子化对策遭遇失败》(日)山田昌弘 译林出版社
提到低生育国家,日本常常是最先被提及的。1990 年,根据日本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可知,日本的出生率降至了历史最低值。在那之后的三十多年间,日本的出生率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进入到本世纪,日本人口开始持续减少。西方社会对日本在少子化现象面前毫无应对之策感到惊讶,而日本的东亚近邻们把日本当作反面教材,十分担心会重蹈其覆辙。
生育属于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它与社会结构以及经济走势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对人们的心态产生着影响。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在《低生育陷阱: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失败》中提到:男性清楚,以自身的收入,一旦结婚并生育孩子,生活水准将会低于父母的生活水准,因此他们不愿意结婚生子。女性则会因为找不到收入稳定的男性而无法结婚。年轻人中这类人的占比在逐渐增大。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是少子化所导致的原因。
从经济层面来看,最重要的是,“日本社会正在逐渐成为一个把过上‘普通’生活当作是自然而然之事的社会。也就是说,日本社会已然变成了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如果无法过上‘普通’生活,就会觉得无颜面对世人,并且会被亲戚、职场的同事以及学校的同学所看不起。而且,从现在日本绝大部分人认为自己是中流阶层这一现象能够看出,日本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普通生活水准”提升了的社会。家电产品齐全这一点无需多言,现在的普通生活还要求(在有必要的情况下)有车,(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住上公寓或者拥有单门独户的房子,让孩子上补习班或者课外兴趣班,能够让孩子上大学。
世界上不少国家的民众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并非日本所独有,即俗称的“内卷”。这会带来一个结果:无法为孩子提供“普通水平的生活”,这会动摇人们作为父母的自信。人们不仅会自主限制生育孩子的数量,而且如果觉得将来无法为孩子提供特定的环境,他们甚至连婚都不会结。
归根到底,少子化社会得以形成,是因为“对未来生活缺乏安全感的一种意识”。日本作为先发国家,是全球最早且同时面临超老龄化与少子化情况的国家之一。少子化社会存在普遍性的成因,像经济的发展以及思想观念的变化等。山田昌弘觉得,“日本政府把欧美的习俗和价值观错误地当作了参考依据,没有留意到当下年轻人的心声以及他们所面临的现实情况,并且在政策涉及金钱时总是行动缓慢。”他接着认为,日本政府的最大问题是对日本社会的养育意识有所忽视,把少子化仅仅看作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没有重视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所带来的影响。要想缓解少子化问题,政策制定者必须看到问题背后的文化意识。同时,政策制定者也必须看到问题背后的社会问题。
东亚社会的内卷在这几年成为热门话题。日本有“平成废物”一代,他们信奉“逃避虽可耻但有用”,抛弃了上进心,活在网络和二次元的世界里。这个群体形成的原因,在于个人向上流动十分艰难,当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时,就只能选择消极抵抗。
日本从平成时代开始,总生育率一直处于 1.6 以下。1992 年的时候,“少子社会”这个词就开始进入到日本社会的视野之中。在此之后,日本在 1994 年制定了“天使计划”,1999 年出台了少子化对策的基本方针,2003 年又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山田昌弘曾写道:从意识到少子化问题的存在,到政府开始着手采取对策,差不多花费了 10 年的时间。事后表明,这 10 年的延误是极为致命的。这些对策没有起到作用。
在现实里,很多人看到结婚率和生育率下降时,总是轻易地说“年轻人太自私,只知道享受,没有责任感”,这种看法明显很仓促。和他们的父母相比,现今的年轻人没享受到全球化快速运转带来的好处,也没享受到早期的社会福利,然而从结婚到生育,成本都大幅增加了。在结婚这件事上,预设了很多物质方面的前置条件,准备工作就已经很困难了。买房和养娃之后,花费都非常巨大。在学位和升学等问题上存在高度内卷,同时又有高强度工作和失业风险,这会劝退无数人。
日本的情况存在差异,然而最直接的原因也是成本问题。并且就如书中所讲,日本文化十分注重“风险规避意识”,注重对生活进行长期规划。所以,倘若结婚生育会致使现有生活水平降低,那么人们就会选择不结婚不育。从日本规避风险的意识角度来看,在交往方面,并非仅仅依据是否喜欢的恋爱情感来决定交往。而是会带着对与对方交往后以及结婚后将来生活会是何种模样的思考,以此来判断是否进行交往。
日本人会主动去为孩子避开风险。他们如果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承担孩子的成长,就不会让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意味着,对于孩子的人生规划,需要在父母结婚之前就开始进行考虑。所以,日本的年轻人不认为恋爱就是单纯的恋爱,结婚就是单纯的结婚,育儿就是单纯的育儿。他们不会等到孩子长大后才考虑孩子的教育费等问题,也不会等到晚年才考虑晚年生活等问题。也就是说,他们不会把这些问题孤立开来对待。
在日本社会,这种责任意识是普通民众所具备的。孩子即便已经成年,父母依然会主动参与到他们的婚育问题中,甚至是教育第三代的问题,从而施加持续的影响。这一现象在日本以及东亚社会都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然而,也正是因为此,日本的少子化程度远远比欧美更为严重。
这种思维与欧美存在很大差异。欧美国家的人们对工作的社会等级差异不太在意,蓝领和白领之间差异不明显,他们不会太在意别人的眼光。而在日本乃至东亚地区,人们普遍很在意他人的看法,并且将他人的看法当作能否立足于社会的最重要标准。山田昌弘写道:在日本社会里,即便事情再好,只要做出的举动与多数人不同,就不会得到肯定。也正因如此,日本非婚生子比例远低于欧美,并且人们思考过多,对风险的预估过于“精确”,那么愿意结婚生子的人自然就会更少。
山田昌弘在书中提及了几个日本社会的细节。年轻男女通常与父母同住。在欧美家庭,年轻人离开父母独立居住是主流情况。生育会带来补贴。这种生活环境的差异,导致日本年轻人缺乏个人空间。所以,日本年轻人很容易将自身缺少空间的困境投射到未来。“通过工作实现自我价值”的观念,在日本女性中也不是很流行。日本社会对职业女性不太友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原因。女性在结婚和生育之后,通常很难再回到未婚未育之前的岗位。
山田昌弘在对大量问题进行分析后,提出了自己的解决路径:需要让绝大部分年轻人确信,即便结婚后生育两个以上孩子,也能维持普通生活水准;同时,要把我们的社会改造成这样一个社会,即无论哪个年轻人都有希望将来能不让自己的孩子受苦。当然,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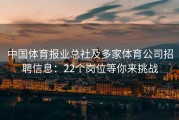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