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基础学科的辉煌与落寞:从贵族学科到乡镇青年的同病相怜
北大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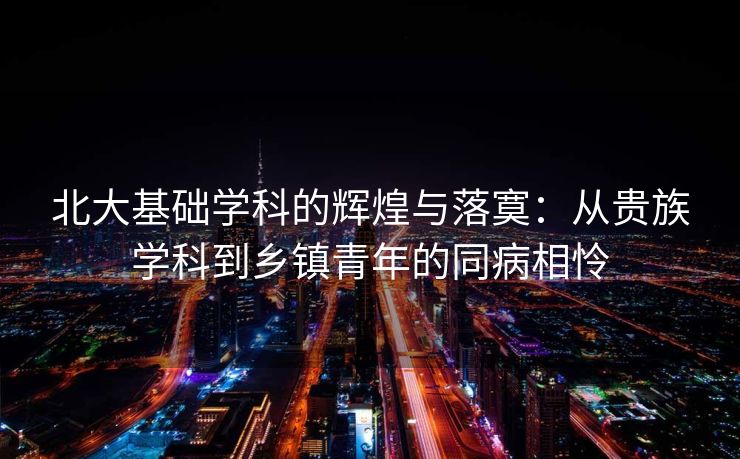
当年我在北大读书时,身边的朋友大多是基础学科出身。在圈子里见面寒暄时,总有一句话是“大慌啊!”这是对疑似持续扎心感的一种客观描述,通常具有在各种尴尬境遇时进行自嘲解围的功能。基础学科原本属于贵族学科。然而在六七十年代,经过一番波折后,我国的贵族阶层几乎被全部清除。新的贵族阶层也未能及时跟上,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情况。于是,一群乡镇青年聚集在这曾经属于前朝遗老的理想国的废墟之上,彼此之间只剩下了同病相怜的情感。所以考古学常常与化学关系密切;历史编纂学经常和图书馆学混在一起;哲学时常与量子物理学关系暧昧;以上这些都把骂光华管理学院所代表的资本主义邪恶势力当作日常之事。
一般来说,贫穷而迂腐的读书人常常喜欢通过偏袒同党、攻击异己来极力刷出自己的存在感。从大的方面来讲,海淀区的高校大致形成了以清华大学等工科方面强势势力为阵营的“环绕成府路的华约组织”,与以北京大学等文理科方面强势势力为阵营的“泛中关村大街的北约组织”相对峙。在北京大学内部也存在着一种很奇特的鄙视链,并且北京大学的鄙视链严格地体现着权力相互制衡的精髓,呈现出首尾相连的状态,从而形成了一条鄙视的环形。光华的天之骄子们时常抿上一口优质的牙买加蓝山咖啡,以一种仿佛帝王般的蔑视神情,从牙缝中挤出一声“傻 beep”。接着,人文学科的的士大夫们则喝下一口价格为两块钱的燕京啤酒,回敬一句“毒瘤”。那时候我的小圈子里主要就是一群穷得很的、以当代士大夫自居的观星者。他们一边穿着拖鞋在燕园里走来走去,一边手不离哈耶克、波普尔和存在主义四大天王的书,同时嘴上唱着《长铗》,还叽叽歪歪地吟诵着“食无鱼,出无车,两袖清风为谁忙;士可杀,不可辱,十年寒窗付东流”之类的话。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大慌。
大慌则进击
大慌乃慌的最高形态。大慌具有层次感。从深层次来看:基础学科出身的人都明白,自己在学科上每进步一分,人类文明的根基就会更扎实一尺,然而那些享受着福利的众多众生却会反过来以怨报德地嘲讽一丈。从浅层次来说:基础学科的学人们下一顿饭究竟由谁来负责解决。
大家都知道,从二十九年前起,基础人文学科一直被视为拉低北大整体就业率的主要因素。然而,这些学科具有典型的高风险高回报特征。文史哲等几大学科,不仅持续贡献着失业率,还造就了众多的企业家和社会名流。在学科内部,基尼系数绝对达到了可能引发革命的高危险程度。
究其原因,人至慌则无敌。有道是穷寇勿追,若现实问题在“术”层面无法解决,就会使这些文人骚客在“道”层面一直裸奔。因为“至慌”意味着已到极限,不可能更慌,所以人就会无所畏惧,思考问题时这群亡命徒会直接冲向本体论,毫无回旋余地。前几天听闻一个谣言,说北大零七级的两千多人去年为祖国贡献了三百多亿的 GDP。这虽是个玩笑话,但我宁愿相信它是真的。不然,天天只知道谈玄吹牛逼,还不自知地拖了同窗们的后腿。所以,醒醒吧,该去搬砖了,这才是正道。我认为这就是时代精神的最佳体现——承认自己说谎,本身就是从说谎迈向镇定的第一步。
二〇〇七年入学的我们这些人如今快三十岁了,到了春暖花开可以有所作为的年纪。当年那两千多个慌张的年轻人,如今有的身着紫袍蟒带,有的挥金如土,有的学富五车,有的碌碌无为,有的削发为僧,有的吞枪自杀,各种情况都有。你眼见他建起高楼,眼见他宴请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见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最近听闻同级外院有个姑娘,借着一百二十年校庆这个由头,卖了一波“北大红”的山寨口红。我心里竟然没有丝毫波澜,甚至还想发笑。
我的同班同窗如今,有的成为了受尊敬的史学家;有的成为了官媒朝堂的发声者;有的成了在资本圈制造风波的操盘手;有的突发奇想创建了一个二次元电台,如今拥有百万用户并开拓市场获利;有的精心经营虚拟币,而后疯狂套现二十亿。我的那些狐朋狗友中:努尔艾力以前是乌鲁木齐的一个胖子,如今他在奇葩说和畅销书榜上都很有名,不是跟着老俞去重走梦想之旅,就是给暴雪做双语电竞解说;此间的少年黄河清活得极为洒脱,前一刻在刚果参与穿越火线活动,后一秒就在巴黎谈商论道,回国后又和我一起搞教育革命;五四球场的那个花样美男,摇了四年试管后去纽约读了四年亚里士多德,现在成了能让成千上万迷妹迷弟哭爹喊娘、砸锅卖铁也要学哲学的凌云老师。
不投缘的彼此就会老死不相往来,而志同道合的则会肝胆相照。这几千人各自有着各自的进击方式,坚持自己的做法才是这所历经百年的老校所沉淀下来的。对圣贤之书研读了十年,要如何在平地上建起高楼,即便一直只是旁观也都能够学会了。那高耸入云的危楼有百尺之高,却能在众多事物中巍然屹立并面带微笑。
再慌就革命
人上了年纪,多读些书,多经历些世事,就会变得刚中带柔且宽容体贴。于是我们追求的是和解,而非当年那种嚣张跋扈到处树敌的行为。作为历史学系的人,我无法在史海古卷中沉醉其中无法自拔,也无法继承祖师爷们的衣钵。最恰当的解释是,内心的大慌使我无法再潜心钻研、在古佛青灯旁度过一生,我要去寻找大定,去寻找和解。几年过去了,身上的文学细菌已变成了满肚子的商学病毒。但做生意并不意味着背叛理想。左手拿着金银,右手握着诗歌,两手都能抓好。如果你仔细观察我发黑的印堂,左右横竖所写的依然都是远方这两个字。
于是我就选择了用务实的商业力量去掀起理想主义的教育革命。
判断一个人是否为纯金北大男,一方面要考察他会不会唱《未名湖是个海洋》,另一方面要了解他知不知道图书馆前那对石狮子的秘密,同时还必须观察他听到“革命”二字时的生理反应。如果他听到“革命”这两个音节,他的面色会泛红,呼吸会急促,瞳孔会放大,仿佛欲仙欲死。那么可以确定他进入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他自认为“王霸之气”已经外泄,分分钟能够驱散京城六环以内雾霾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是非常确定的。
然而仔细想想回归现实,搞教育革命这一情况根本就是个伪命题。因为在三千年的时间里,欧亚大陆的教育仅有那么几种方式:
要么是雅典学院一系的苏格拉底问答法,它开启了古典贵族的慧根,为哲人王正了名,使其圣光能够普照。而其他生来就被注定命运如破铜烂铁的围观群众,就赶紧去睡觉吧。听他们在那忽悠,要是我是雅典的市井小民,我也会感到慌乱。
弗洛伦撒中世纪大学的一系从事拉丁密宗的医学、法学、神学职业技术培训,还将其美称为分别治疗身体、社会、灵魂。然而,这一轰轰烈烈的“这是病得治”的思路最终回到了罗马本营,身体、社会、灵魂依然那么肮脏,反倒让道貌岸然的天主教廷被好学生马丁·路德的小短文给革命了,令人慌张。
要么是卢梭、康德、罗尔斯这一系与你谈论左翼进步青年的情怀问题。经过三百多年的论证得出结论,制度无法解决的事情都要依靠公意、人性和形而上学来解决。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要充分发挥自身天性中的同情心和同理心,多进行换位思考,不要总是用屁股来决定脑袋,也不要对洛克、孟德斯鸠那帮人每天叫嚷的制度胜利太过在意。对于不抱一丝幻想的自由右派而言,左翼进步青年的亢奋状态早已被归入大慌派豪华午餐系列之中。
孔夫子和门修斯这一系,一方面秉持“有教无类”,另一方面又强调“君臣父子”,他们在思想领域横挑法墨,在社会秩序上竖统释道。历经漫长的三千年,他们不探讨为何要这样做,只是教导人们如何去做。通过这样的教导,培养出了一群大学霸,这些人在乡会殿试中表现出色,如同一条龙般顺畅,最终获得翎顶红袍,仕途一帆风顺,以至于君王都不再早早上朝。那气势极为磅礴,即便西方那些武装到极致的先辈们曾欺凌我国上百年,他们也只能强忍痛苦咽下满嘴碎牙,挤出一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代宣言来自我安慰。然而,自我安慰终究不能等同于自我防卫,在一阵强烈的满足感过后,留下的仅仅是无尽的慌乱。
所以说,教育原本就无需革命。因为先贤往圣早已想到了该有的方案,不同之处仅在于你是否会运用这些教育工具包的组合技。在教育的命题中,我认为终极理想是要切实地借助知识的力量去解决大慌的问题。这绝非革命,而是一个古老梦想的光荣回归。
断慌源
斯密告诉我们要尊重那只难以分辨左右且看不见的手;李嘉图告诉我们应做自己擅长的事,发挥比较优势去进行劳动分工;哈耶克告诉我们广义的知识如同春江水暖鸭先知,摊煎饼果子的大妈比皇帝更懂市场。所以若要搞教育革命,就必须与经济学院和光华和好,对经济规律表现出起码的尊重。教育革命并非是那种大义凛然、赴汤蹈火般的作秀。要让在世俗泥沼中艰难求生、啃食泥土的苦难人民对百年大计有所憧憬,就必须先让大家尝到眼前的好处。无论象牙塔里的那些抽象学问有多么重要,将一部分知识的糖精进行稀释,让更多的人喜爱上它,并不会耽误知识殿堂的建设进程。所以,现阶段抽象知识的生产力是关键所在,关于有用还是没用的争论最好先搁置一边。
我认为大学里的老先生们并非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是他们大多不太清楚所教授的这些知识在哪个关键的时刻能够转化为生产力。在我从小到大上过的各种大小学校中,教我的人无非都是在体制内待了很久的人民教师。倘若我几十年不接触社会现实,大概也会忘记生活中的苦辣酸甜。其实接受高等教育有两条出路。其一,留在高等教育当中,持续以非常抽象的方式保存和优化人类智慧的精华。其二,从高等教育中走出,接着把人类智慧的精华带出来,以非常具象的方式转化为源源不断的生产力。说白了,广大的大学毕业生其实就是在壁垒森严的学校之墙间自由进出的搬运工。他们用墙内的黑武器元器件搬出来,制作成墙外的黑武器。
只是,校园中负责制造元器件的人民教师们倘若自身也不懂得如何组装这些杂乱无章的零件,那确实会非常麻烦。就如同生产商把砖石、水泥、钢筋、电线、水气管道都包邮送到家,接着告诉你说“好了,把它们拼到一起就变成豪宅了”。你询问是否有组装说明书之类的东西,他们回答说:“很抱歉,我一生都在专注于研究砖石、水泥、钢筋、电线以及水气管道等,从未参与过盖房子的工作。”你眼睁睁地看着这满地的破烂在岁月的流逝中逐渐消失。接着你说,如果要盖房子,砖石、水泥、钢筋、电线、水气管道这些根本就没有用处,只需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等待长辈们分配一套茅草屋、舢板子房,甚至是地洞,那些乖孙子们也能居住。然后,砖石水泥钢筋电线水气管道的生产商自然心里不太愉快。接着,整个话语的风格就转变到了价值论的范畴。他们说这些砖石水泥钢筋电线水气管道本身是美的,而你们这些普通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和他们愉快地交谈。
北大精神原本不在朝,而是在野。倘若老先生们真觉得神圣的知识不能被世俗沾染,那就可以把脏活累活交给我们这些路子野的燕园解放组织的叛党。因为在这些“被玷污的”知识所启发的年轻人当中,就有未来挑战人类智慧巅峰的接班人。要让这些年轻人全心全意地做学问,我们最好先帮他们断绝慌源。
不慌了
我回忆了一下,当年在燕园里,那些我爱的、恨的、纠缠不清的、一丘之貉的老相识和老相好们,其中竟鲜有商科和经济科的校友。到了今天,看着自己的商业化教育项目每年有八位数的进进出出的各种账目,我们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天天研究的哲学命题还可以这样去落地实践。这着实让我觉得,当年那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是多么幼稚可笑。当年认为商学这种显得浮华的知识以及浮躁的学问不值得耗费时间。如今真正亲身去接触后,才明白原来这看似充满诱惑的知识,是那些看上去没有用处的哲学之根所开出的美丽花朵。然而,术业依旧是有各自的专攻,哲学之根与商业之花一个都不能缺失。只是这个道理是最近才领悟到的,而现在要是有问题想找专业人士请教一下,却变成了一件难事。
前几天在波士顿街头碰见了一位商学科班出身的故交,我询问他在做什么生意。他叹了口气,说现在生意进入了瓶颈期,索性关张几年。他还说现在的感受就是当年我们常挂在嘴边的那个词,大慌。我笑着问他闲下来要做些什么,他说自然是要恶补一下哲学和历史了,因为头破血流之后才知道商业之根在于此,他后悔不该当年如此鄙视这些学问。
我愣了一下。我觉得北大那些看似穷酸迂腐的士大夫和装腔作势的天之骄子们,终于达成了和解。在那一刻,我一点儿都不慌张。
船长 葛旭
望 皇都繁华
观 麻省肃寂
正文至此结束了。眼下,孤阅有三大学院的课程。这些课程可以向诸位心中的慌源发起进击。我们秉持格致的精神,博采万国的学问。就像巨鹰坠落,烈火燎原一样。那是在漫天繁星闪耀的时候。
孤阅三大学院鼎立
格致学院 |万国学院| 燎原学院
- End -
本文图片源自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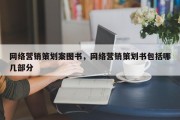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