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岁的00后,用10岁头像,别人以为是我亲儿子!
你的微信头像是什么样的?
前段时间,微博上有一个话题叫#老达达不卡的头像#。 一位网友的回答很受欢迎:“等我长大了,我就不敢再用萌娃当头像了,怕被误认为是我自己。” 生的。”
底下不少人都表达了同样的感叹:“我29岁了,用10岁的头像,别人都以为他是我的亲生儿子。” “我现在用的萌娃头像已经陪伴我三年了,最近要去相亲,应该不能换了”……
这些网友的调侃表明,有大量的人热衷于用可爱的婴儿或卡通儿童作为自己的头像。
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无论你是初出茅庐的00后,还是已经成为职场老手的90后; 无论你还是单身,还是为人父母……在选择微信头像时,他常常默契地呈现出可爱又傻气的“宝宝”模样。
用可爱的网红作为头像的人不在少数。
如今,随着社交媒体的上线,我们的大部分交流都是通过社交应用程序完成的,不需要面对面的接触。 微信头像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我们的第二张脸。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作为成年人,仍然选择用儿童的形象来代表自己呢?
01
你仔细研究过大家的微信头像吗?
前段时间,半夜失眠的小海打开公司微信群,观察大家的头像。 他突然发现,公司109人的群里,有19人的头像是“宝贝”(不是自己的孩子)。
出于无聊,他对这些头像进行了分类:6人用的是自己小时候的照片,7人用的是网红、可爱小明星的照片,另外6人用的是史努比、哆啦A梦等图片。 卡通“孩子”,如拉阿蒙。
为了验证此事的普遍性,我随机抽取了不同工作单位的10人进行了抽样调查。 最后发现,这些萌娃头像的人占了整个通讯录的1/10。
也就是说,每添加10个人,就会有1个人拥有萌娃头像! 更何况还有一些频繁更换头像的“换头者”,甚至在某些时候还使用过萌娃头像。
其实就像“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一样,人们对萌娃的喜爱几乎是本能的。
奥地利动物学家康拉德·洛伦茨曾提出“幼虫保留”的思想,即喜欢一切具有幼虫特征的东西是人的天性。 幼儿的可爱自然能够引起大人的喜爱,这保证了幼儿能够得到适当的照顾。
当然,除了对“可爱萌娃”的本能喜爱之外,萌娃微信头像还包括我们在网络社交空间中形象的构建。
与日常现实生活中的交流不同,微信社交是一种典型的缺席交流:我们无法直观地感受到对方的表情、神态、语气,因此微信头像成为了最重要的社交印象载体,甚至可以说是社交面具。
加拿大著名社会学家戈夫曼在研究人们的社会行为时曾提出“戏剧理论”。 他认为社会就像一个舞台,人们的社会行为就是社会表演。
在交互过程中,人们按照一定的常规程序(即脚本)扮演各自的角色。 在表演过程中,人们试图控制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用言语、手势等表情使别人形成自己想要的印象(称为“印象管理”); 为了实现印象管理,人们使用一些手段(外部设施和个人装饰)来装饰门面。
同样的,我们的网络社交平台也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交舞台。 通过可爱的宝宝头像,我们很快找到了在社交平台上宣传个人形象的最佳方式——一旦施展可爱的魔力,无论多么平凡的事物,都会很快充满亲切感。
如果你不相信我,想象一下你第一次通过微信认识了另一个人。 如果对方的头像是一个可爱的小孩,那么你的第一反应应该不会是觉得对方是一个多么坏的人吧?
02
如果要追溯人们使用萌娃作为头像的习惯,应该从2013年的韩国综艺节目《超人回来了》说起。
这档综艺的火爆,为微信提供了大量经久不衰的表情包。 富有表现力、聪明又略带傻气的郭敏突然成为中国网民表情包和头像的“供应商”。 人们高兴地从演出中捕捉到民国的表情。 当然,很多人直接用民国作为自己的头像。
随后,《爸爸去哪儿》在中国播出,每一季都有几个孩子悄悄成为人们的微信头像。 去年,随着第五季的播出,陈小春的儿子Jasper一炮而红。 当时我的微信通讯录里就可以找到几个Jasper宝宝。
不用说,可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爱的特征之一。
不仅如此,从社交媒体到实体空间,各种图像和符号都被添加了“可爱”的“香料”。
看看近几年的服装箱包品牌。 哪一款没有和可爱的卡通人物联名呢? 看看路上的行人。 谁的包里没有绑着各种小玩偶或卡通人物? 就连手机壳也总是装饰着各种卡通人物。
这一切都证明了越来越多的人对那些可爱的东西有着深深的喜爱。
在中国,社会学家将其概括为“可爱文化”。
20世纪初,美国社会掀起了一股儿童崇拜风潮。 当时,人们开始反思和批判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儿童的世界被视为与成人世界完全不同的纯洁无邪的世界。 在工业社会里,它有一层纯真和向往。

与此同时,描绘乡村幸福生活和各种可爱的人物和动物的迪士尼动画,因其充满童趣,迎合了人们对过去天真无邪生活的想象而深受人们喜爱。
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迪士尼动画进入日本。 天真单纯的内核与日本以纯真为美的文化传统产生共鸣,同时也抚慰了战后人们破碎的心灵。 由此,日本衍生出了“二次元”、“萌宠漫画”等“可爱文化”。
近年来,通过二次元文化的传播,类似的“可爱文化”不断从日本传播到韩国和中国。
随着消费文化的发展,我们看到微博上萌宠博主和爱猫帮的数量不断增加。 在朋友圈炫耀、炫耀、卖萌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各种可爱的动物、萌娃头像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日常交流系统——可爱文化开始在中国形成自己的形态。
03
从人们对萌娃头像的热衷来看,其实人们对“可爱”的渴望和追求几乎无处不在。
近年来,大人喊着过儿童节不再是自嘲式的玩笑,而是通过一系列“呼、礼、穿、吃、喝、消费”等实际行动。 在社交媒体上。 以“三维”方式做一个孩子。
事实上,成人世界中“假装年轻”、“回到童年”的迹象早年就已经出现。
最近,前年《小猪佩奇》的火爆被发现。 人们发现,让这部动画片走红的人并不是目标受众的孩子,而是二三十岁的成年人;
儿童节不再只是孩子们的合法节日。 大人们也加入了童真狂欢,占领游乐园,玩儿童游戏。
市场品牌也趁机掀起怀旧童真风潮。 扭蛋机、捉迷藏、跳格等游戏已成为品牌营销传播的创意形式。
这些现象频繁发生,并逐渐蔓延成一种青少年亚文化——国内学者称之为“成人化”。 用可爱的婴儿头像装饰自己的社交“门面”,实际上只是“大人儿童化”的一部分。
可爱文化背后“大人化”现象的兴起,并不单纯是因为人们本能地喜欢可爱的东西,而是因为它在某个点上击中了现代人的情感症状。
这种“成人化-儿童化”往往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者的集体怀旧情绪。
在网络音乐平台上,我们经常看到这种对童年的怀念。
比如罗大佑歌曲《童年》的评论区,出现频率最高的评论是“小时候”。
有网友写道:“小时候真棒,在乡下河里游泳,抓龙虾,钓鱼,吃2分钱的冰棍,1分钱的辣条。我们不追电视剧那个时候,我们就看电视上的节目。没有手机,没有WIFI,我们仍然玩得很开心。做个孩子真好。”
翻看这首歌的热门评论,大多都是伤感、怀旧的。
对于处于中国现代化转型最前沿的年轻人来说,过去的时光流逝得越来越快,激起他们对童年、青年等记忆中美好时光的怀念。 因此,对童年的怀念成为他们抵御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的防御机制。
由于现代社会快速运转带来的巨大竞争压力,年轻人在寻求稳定生活的同时不断质疑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正是现实的痛苦,让大家产生了怀旧的冲动:在刘昊霖的歌曲《童年》中,有网友评论道:“小时候,我总是骗父母说我没有钱,但现在我骗他们说我还有钱。”
因此,我们渴望回到童年,成为那个自由的孩子,治愈现实带来的痛苦——至少改变自己能力范围内的化身。
当晚,失眠的肖海在给大家的头像分类后仍然没有睡着,于是他点开了同事艾丽的头像。
艾莉已经5年没有换过头像了。 她的头像是电影《好看》中的小男孩方强强。 剧照中,方某腰间插着枪,嘴角撅起,一脸愤怒和委屈地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老师,正要惩罚他。
艾黎觉得自己每次都能和方强强找到共鸣——无论这个世界有多么残酷,他还是要嘟着嘴装可爱。 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双手叉腰,勇敢面对。
或许对于大家来说,用孩子的头像武装自己只是装可爱,博取好感,但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微信头像中的孩子就像守护神一样,给予年轻人力量。继续你的社交生活。
-结束-
本文经“新周刊”微信公众号(ID:new-weekly)授权转载。 《新周刊》创刊于1996年8月18日,定位为“中国最前沿的生活方式周刊”,二十多年来用前沿态度丈量时代温度。 从杂志到新媒体,《新周刊》不断寻找你我共同的痛点、泪点和笑点。 关注新周刊微信公众号,与你一起生活有态度。 官方微博@新周刊。封面来源:古龙
贡献与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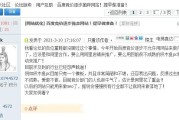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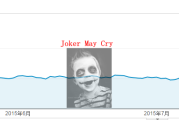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