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幕组掀起翻译界革命,改变流行视觉文化和观影方式

一排14到20个汉字,停留5秒,是字幕在观众视野中的极限。
这行不起眼的文字掀起了翻译行业革命的又一个高潮:字幕组由此应运而生,并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改变着流行的视觉文化和电影观看方式。这种在灰色地带运作的神秘组织,因其独特的内容生产链而获得了极高的需求量。
5月12日,在杭州单程空间举办的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图书品牌“甲骨文”主办的第二届翻译论坛《翻译与我们的时代》上,中文系教授严峰、闯李复旦大学特影视翻译创始人钱宁与资深影评人梅雪峰就他们心中的“字幕组”以及影视翻译的标准展开了对话。
好字幕,难道就应该看不见吗?

严峰
严峰介绍,中国历史上有过四次彻底改变历史文化的大规模翻译活动:一是鸠摩罗什、玄奘组织的佛经翻译,创造了历史;二是鸠摩罗什、玄奘组织的佛经翻译,创造了历史;二是林钦南、严复对近代西方文学、艺术、文化的翻译改变了近代中国的进程;第三次是“文革”后,商务印书馆、外国文学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上海翻译机构翻译西方现代文化思想著作,推动了改革开放,带来了众多受益者;第四次是新世纪草根字幕组,掀起了新一轮翻译革命。

宁谦
宁浅认为,好的字幕应该是看不见的。电影的核心在于导演的视觉语言、构思和对话,而不是字幕。优秀的字幕应遵循翻译最根本的原则“信、雅”,尽可能忠实于原作,让观众无障碍地欣赏影视作品。
“字幕就是弹幕,弹幕某种意义上也是字幕。”严峰表示,今天的字幕是作者导向、服务导向、辅助导向,可以单挑画面与观众交流。在B站看视频时,经常可以看到向字幕组致敬的弹幕,相当于字幕和弹幕合二为一。在传统观念中,译者应该是“透明的”。当今时代,译者变得更加大胆,以积极、有趣的方式与读者和观众对话。这是否意味着古典翻译时代的结束?未来,译者会不会通过这些一排排黑字来展现自己独特的个性,而不是被动接受?
在梅雪峰看来,字幕组是时代特有的产物,也是知识共享的副产品。随着时代的不断流动和开放,翻译不再是精英阶层的专利,而是成为全民的公共参与。 “一切都是翻译,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片,都是思想的翻译。当你选择浅焦镜头时,你的镜头对准人物,将人物无限放大;当你选择深焦镜头时,你的镜头对准人物,将人物无限放大。”人物被拉远,景深成为镜头的主体,看似是画面,其实却转化了你对世界万物的理解和思考。”

梅雪峰
翻译电影将走向何方?
严峰回忆说,他的童年是在翻译电影中度过的。年轻观众几乎无法忍受翻译电影的“翻译口音”,想听听原声。曾经辉煌的翻译电影如今已经进入了暮年。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翻译电影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当时的进口片数量很少,演员的名字也很少有人知道,但配音演员是谁却是大家都知道的。他最念念不忘的,就是邱月枫沙哑的声音。后来,邱跃峰因故自杀,令他久久难以忘怀。
作为铁杆“仇粉”,他首先想起仇越峰的声音,就是出自著名的《追击》。当他第一次看《追击》时,他发现自己的眼睛已经近视了。回到家后,我翻箱倒柜,找到了父亲的近视眼镜,威力太大了。我把奶奶的老花镜叠在上面,在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将它们组装成危险的“组合眼镜”。然后我又回到了剧院。时光荏苒,但他对邱岳峰配音的那句名言的印象却丝毫没有改变:“杜丘,你看天多蓝,一直往前走,不要东张西望,走过去,你就会融化”进入那片蔚蓝的天空”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配音电影正在消失,二次元、动漫、游戏等新兴配音文化随之兴起。配音行业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 “我们很多人曾经对那些坚实、饱满、精雕细琢的石音有过一些难忘的记忆,而那些记忆却在慢慢地、无奈地被现实腐蚀。我们曾感叹文字的没落,我们都在感叹言语的没落,但我还是想把美好的声音留在记忆中,做一个过时的语音中间派。正是他对翻译电影的迷恋,让他成为了一名严肃的声音学家,无法快速融入图像时代。
梅雪峰认为,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太容易找到相似的人,这会导致不断的反馈和相互强化,形成精神防火墙。每个人都被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所束缚。从表面上看,互联网让每个人都发生了改变。它变得越来越开放,同时也变得碎片化。翻译电影可以打破这种文化障碍,将两种不同的文化融合在一起。
“配音是一种背叛,更是一种创作的背叛。”严峰说,“我们需要翻译、字幕、配音。这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种语言、一种声音,也只有一种思维。不同语言在翻译中和思想混合、碰撞、交流,形成融合、对话和冲突,这就是生命的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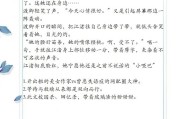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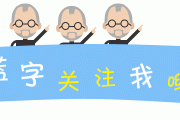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