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尚晓岚同志离世,退邮包裹刺痛人心
就在前天,我收到了一个回邮包裹,上面写着“朝阳区白家庄东里23号A座北京青年报尚晓兰同志”。这是我们每期发给小兰的包裹。免费《读书》杂志。即使我了解邮政术语,当我看到信封上手写的“未找到此人”时,我的心还是很受伤。这种感觉就像3月1日早上一样:经过一夜的焦虑、无助和幸运之后,我清楚地记得听到最后的坏消息时喉咙里的血腥味。
小兰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两个多月了。这期间,我一方面收集朋友的文字和图片纪念她,另一方面又极力回避她的离去,不敢轻言,难以下笔。没有机会正式和她告别,每次在街上看到和她发型、身高差不多的女人,我都会有片刻的发呆。接下来打击的是支离破碎的现实。如果说人生如画,我想这就是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给我留下的“留白”。

左一为参加活字文化“活字π”活动的商晓兰
认识小兰,大概就像所有认识她的三联人一样,我们是通过书籍和出版结缘的。但真正熟悉它是2013年调到《读书》之后才开始的。小兰经常来三联书店。平时她每次来,都会忙完工作就跑到四楼《读书》编辑部来找我。我们会在三层楼的屋顶上抽烟。从屋顶上可以看到北京古城,天气好的时候甚至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小兰很喜欢这样珍贵的老城风景。就在这里,我们一直聊天。她比我年长,又在体制内媒体担任编辑,所以她对我和杂志社可能遇到的困难有先见之明。而她善意的安慰和有力的鼓励,就像她善良、坚定、俏皮的印象一样,绝不会让谈话变成对周围环境的抱怨。

尚晓兰在三联书店,2006年
在我“学习”的六年里,小兰给了我很大的、甚至是无条件的支持。 2014年至2016年,她保持了每年一篇文章的发表速度。 2017年,一篇长文被拆分成两篇独立文章,标题为《审问“恶魔”》和《来自彼岸的呼唤》。不过,从那以后,她就专心致志地改写了《中书令司马迁》的剧本,修改发表了两篇文章,就暂时搁置了,也没有催我(直到最后我们在三联见面)去年12月份,她还主动帮我缓解了此事)的压力。没让她看到出版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遗憾)。她参与了许多关于《雷丁》出版或不出版的讨论,更不用说每年的作者社交聚会了。记得2016年初,当我们刚刚建立“读书”微信公众号时,我们非常热情,邀请了三位年轻作家为我们写协会通讯,其中包括小兰。她对那天的活动非常高兴,并告诉我她有一个独特的角度可以写。我连忙说,只要你乐意写,公众号任何文章格式都可以。最后,她写了一篇充满“怪医黑杰克”和“神奇美少女”的文章,名为《三重二维世界》(最后三篇简讯以总标题“三重作者的氛围”发表)开会就差不多这样了”,用的也是她文章里的一句话)。这或许是难得的一段与小兰对动画浓厚兴趣相关的文字,而她当时使用的笔名“常守主”,正是她微信头像的原型。
这几年,我和她,还有桃子,只要有需要,就会聚在一起,谈论各自的思想、文化、文学的看法。两人聊了很多,我在一旁充当配角。在那几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下,我们在咖啡馆、酒吧里的谈话显得格外不寻常。思考者或许注定是孤独的,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氛围,这种对话才显得更加珍贵。我想这可能就是小兰喜欢《读书》杂志的原因吧。她对我的支持,其实是基于她对《读书》本身的感受。今年是《读书》出版40周年。去年我想编一本书,叫《读书和我》,受邀投稿的作者之一是小兰。她欣然同意,并且是最早提交手稿的人之一。在这篇题为《四十岁仍迷茫》的文章中,她回顾了自己中学时阅读这本杂志的经历。她特别看重《读书》的特殊风格,使她免于尝到一般文学中的“美文”的味道。出来了;但她20世纪90年代参加工作后,中国正在发生深刻而迅速的变化,《读书》的出版风格也有所创新。她读着它,研究着它,甚至开始欣赏它,但又不失内心的平静。为之而写。她说:“《读书》的文章只有‘三不’——没有问题不写、没有感情不写、没有感情不写” 《读书》迄今为止发表的七篇文章,都是如此。读完她身后的这七段文字,相信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点。

《今日》2018年1月第117期
思想的孤独并不意味着沉默和安静。必须承认它也是锋利的。有时尖锐到紧张,有时尖锐到变成敌人。这样的情况在中国过去二十年的意识形态讨论中并不少见。 《读书》杂志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样的漩涡,在人们的流言蜚语、猜想和满天飞舞的标签中漂流前行。小兰当然有她自己的立场,她也看重自己思想的品质和力量。但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合,她都不会因为立场的不同而胡言乱语(这并不是因为她世故,而是因为她懒得让自己的心思过多地纠缠在所谓的“人事”问题上),更何况她可以做出选边站队之类的简单言论,但她更愿意去发现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无论是在谈话中还是在文章中,她其实都不会直接下结论。相反,她常常对自己产生一些犹豫和反思。这使得她近年来的文章也带有一定的思想“留白”。
小兰最早在《读书》上发表的是2004年的《契诃夫的世界之外》。后来又回顾了田沁鑫改编的《桃花扇》(2006年第8期,题为《无谓的损失》),以及张艺谋的电影《一个人》。 《金甲满城》(2007年第6期,题为《金子也不发光》),李安电影《色·戒》影评(2008年第4期,题为《不谈情,只讲情》)爱情?”)等,都可以看作是她对当下文艺作品的回应。自2014年出版《作为冷战小说》以来,她通过文艺作品写的“思想”问题越来越多,写作格局也越来越大。我还记得2015年冬天第一次读到《荒原狼的嚎叫》初稿时的激动,里面的句子就像钢琴键一样,一个又一个敲进我的心。我们进行了一些讨论,她一度将其扩展至8600字。我觉得语言风格有点不平衡,就让她删掉到6800字,就是出版时的样子。我注意到她删除的地方都是那些会给人“站着”错觉的部分。我认为这是她有意识的决定。而剥去“左”“右”的外衣,她的说法确实更接近问题的本质。难得的是,她还保留了一些自己无法处理的非结论性讨论,但却能启发人们继续思考。在我看来,这样的“留白”的价值,不亚于一座不顾一切的宏伟建筑。这是她的真诚和谦虚,她的野心和态度。小兰曾在一次针对《中书令司马迁》剧本的青年学者研讨会上表示,这个剧本永远都有修改的空间,可能“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在她的思想论文中,这样的“留白”也是一种未完成的作品,应该有类似的思想和结构。当然,这也包括她写作时确实感到困难的地方。

尚晓兰
造成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小兰写作时关心的问题和对话的对象都是非常宏大、尖锐、有理论渊源的问题。她的思考很激烈,但写作时不喜欢使用理论武器。她更注重艺术直觉和经验理性。她更喜欢让自己思想的节奏恰到好处地附着在平实的语言和真挚的感情的表达上。她要达到的就是“字如心声,文如人”。写作到达高山时,不是靠修辞技巧巧妙地滑过去,而是承认克服它的困难。这不是小兰天赋的限制,而是她的珍贵。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些文章,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困难都是历史纠葛的大问题,是人心中的血与火、痛与乐!如果没有她话语的指引,恐怕我们很多人永远也无法到达这座高山。
小兰的《读书》文笔一直在进步。在编辑小兰的稿子时,我不敢轻易做任何事,总是鼓励她自己做一些减法。而每次读她发来的修改版,无论上一版与上一版相隔多久,我都能看到明显的变化:要么文字更加轻松,要么表达更加谨慎分寸,这让人们更有信心。人们可以感受到她的付出和努力。因此,我总想,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脑海里的“空白”,也许有一天她会自己把它填满。小兰不是学者,不需要为职称或晋升而写作。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她出于对思想和文学艺术本能的热爱,为《读书》写了这些文章。 1978年以后,中国逐渐开放公共生活空间,在此后的二十年里,出现了相对宽松的环境。这里曾经诞生过许多非常杰出的思想文化人物。然而,随着市场化和流行文化的兴起,许多过去的“潮流引领者”和今天的成功人士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锐利,甚至改变了生活方式。这影响了近一两年中国知识界的面貌。但小兰却有意识地做一些别人不做的事情,以此作为一种爱好。她始终保持着“求知思考的快乐”和“与社会相处的紧张感”(四十岁的《依然迷茫》)。她才华横溢,写作时直面问题,这在当今时代极为罕见。而她在《荒原狼的嚎叫》中对“新文学艺术”出现的呼吁,则发人深省;但她写的这些文章也代表了一种新型的“思想文化批评”,一种超越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批评。对时代文章风格的新探索,通过文艺作品连接时代重大思想命题的可能性,绝对可以成为未来《读书》某类型文章的代表方向。
我曾经询问并猜测过,《中书令司马迁》修改完成后,小兰接下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我曾经对小兰作为一个思想家和作家抱有各种各样的期望。
不幸的是,这一切都戛然而止。

尚晓兰
这是一种“未完成”,也是另一种被迫的“完成”。小兰留下的这些文章和创作,其实已经足以证明她的能力了。但我越能证明这些事情,我就越为她的生活和思想中的“空白”感到难过和难过。
2019 年 5 月 11 日
结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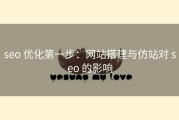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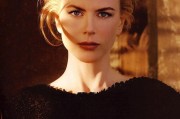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