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凡人歌:从成功人士到社会中下层的回归与反思

吴浩/文怡
前段时间播出的电视剧《凡人歌》讲述了几对不同年龄段的情侣在当下社会中的酸甜苦辣的故事。其中,主角那威是一家新公司的“创始人”。当荧幕上的其他男女在北京写字楼里加班加点,思考着出租房的选择时,这个男人却一帆风顺,事业家庭都不错。唯一的疑问可能就是老板给的选项有点寒酸,不过这个没关系,毕竟我们是兄弟……当然,为了契合电视剧主题,这种顺利就一定会发生意外:被兄弟背叛,被领导操纵,直到大结局前半段,这个忠厚老实的男人还陷在患得患失的状态中,从坐在办公室到做外卖小哥,卖卤肉,一次戏剧性的转变,他终于变成了“凡人”。
这种从成功人士回归社会中下层,用剧中人物的话说就是“活得虚浮,不踏实过往”。豪多斯·韦斯(Howdos Weiss)在《我们从来不是中产阶级》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解释:中产阶级是短暂的,需要不断努力来维护和维持其社会地位。评论家张定浩在评价近年来的青年小说家时,提到了这样的观点:读者(观众)容易对自己不熟悉的经历产生“审美退化”,会对发生在不熟悉的地方、不熟悉的行业的故事置之不理。要求低。与《凡人之歌》一起共同提升普通人标签的文化事件,是图书领域一批所谓“业余写作”的崛起。 “我在北京送快递”、“我妈妈是一名清洁工”、“我在上海开出租车”、“我笨拙地爱这个世界”……写作突然变成了像制作短视频一样几乎零门槛的技能。 ,上述这些作品席卷了去年全年各大阅读榜单。

“我们从来都不是中产阶级”
[作者] 霍多斯·韦斯 |
蔡一能译 |
艺文知识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4 年 1 月
这些来自一线工作者的作品很难按照现有的文学类型来界定。它们都有一个接近非虚构的外壳,这与报告文学中的第三人称姿态不同。他们无一例外地使用第一人称视角来引导故事。读者近距离接触一些熟悉和陌生的职业。传统文坛自然“震惊”。继20世纪80、90年代的“农民工文学”之后,以描述社会工作者为主的文学作品再次出现,但“业余写作”的野心远远超过了它。前辈们,在知识普及、创作门槛降低的大趋势下,《欢颜》的“成功”必然会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开始写作。
二
“北京我送快递”的火爆,是一个时代的征兆,也是一个奇观。不久前,焕颜的第二部作品《低处生活》问世。基于持续不断的流量,非常系统地解答了读者对第一本书和他个人经历的好奇。新作中虽然没有撕心裂肺的苦难,但焕颜作品中的“苦难”却始终渗透在看似平淡的叙事中。因为他一事无成,地位低下,所以他很平静。这个与世隔绝的普通人选择用文学来逃避自己的命运。
《住在下面》
作者: 焕颜 |
普瑞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4 年 8 月
与之前的《送快递》不同,焕颜的坦诚似乎是在为读者分析他的想法。他至少十年前就开始写作,阅读了大量的文学经典。他根本没有任何专业背景或指导。的情况,一直到今天。尽管他自嘲自嘲,认为自己不善于表达,不喜欢社交,但写作的姿态本身就暗示着渴望别人的关注,隐晦地隐藏着与他人交谈的野心。他常常觉得一些知名刊物上发表的文学作品不值一提,但他拒绝将自己归类为作家。这种清醒保证了他的独立性,他可以随意谈论这个圈子的实际贫困。
至于他为何固执地选择了文学,他是这样说的:“写作似乎是没有成本的。”如果绘画、摄影需要昂贵的设备和耗材,焕颜不会选择写作。当然,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贬低。论写作技巧,他在写此类题材时,无法与袁凌等知识分子相提并论。但写作本身其实是对敏感灵魂的召唤,一种自发的召唤。而响应号召的呼声与学历、社会地位、财富无关。
从一个资深文学读者的角度来看,桓彦所输出的中外重要作家的观点和感受并没有什么特别或新鲜的地方,但他扎实的阅读基础,他遵循规律的态度,以及最重要的重要身体素质。永远“生活中”的经历一起完成了普通人写作的里程碑。尽管他本人并不承认这一点,但桓彦的“成功”实际上证明了一个吊诡的命题——传统纯文学其实不存在任何障碍。虽然这个圈子之内有所谓的座位和序列,但是普通人是可以进入这个圈子的。这个圈子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天赋或背景。可能存在的唯一门槛是对“时机”的需求。在这个由于MFA创意写作的兴起而变得越来越复杂的赛道上,胡安彦需要得到平等的对待。它需要被人看到、被讨论,而不仅仅是作为奇观放在畅销书排行榜上。
三
如果说桓彦有一种作家的自觉,那么张小满则有另一种业余写作范式。 《我的母亲被净化了》出版后,我感到非常惊讶,部分是出于对陌生经历的好奇,更多的是钦佩——她指导着文化水平有限的父母写作。我试图在豆瓣上联系她,她慷慨地告诉我,她将来可能会出版一本关于她父亲的书。春香(小曼的母亲)来深圳打工后,她的父亲也开始在深圳从事保洁等基层工作。
张小曼的特点是她的作品有一种微妙的平衡感,没有一丝暴力和挫败感。春香的工作经历曾在政府单位、大型商场、住宅小区工作过。很多细节都是她精心挑选的,就像一本工作笔记本。然而,正当你陷入单调、无聊的时候,母亲在家乡商洛打工的经历的闪回,让你看到了中原人的坚韧和拼搏。她通过春香的眼睛,向你展示深圳这座大城市的毛细血管,尤其是那些位于热带雨林底部、见不到阳光的部分。在春香眼里,那些在底层和顶层之间来回穿梭的电梯,和河南的矿井建筑没有什么区别。这种时而跳出书页的遐想,令人兴奋。
当然,像清洁这样的体力活,必然会有很多的不满。一是工作本身的性质,二是社会共识赋予它的级别本来就不高。但春香却以极大的精神完成了这项工作。从一开始的矜持,到变得经验丰富、能力强,张小满并不是一个居高临下的人。她从一开始写作的动机就是记录母亲离家出走到深圳打工的过程。渐渐地,她也被春香感染,参与到妈妈的日常工作记录中。
作为女儿,她出现在春香的工地时,常常会引起其他保洁员的羡慕。正如她作品中所流露的平衡感一样,她也通过自己的实践实现了对生活和工作的一种和解。 “外包用工模式几乎适用于深圳的每一个大型商场、每一个‘美丽’的公园、每一座高端写字楼。深圳几乎所有的保洁、绿化工作都是由一群50岁到50岁的人来完成。 60、他们身边的老人来自广西、湖南、四川、江西、河南、陕西……如果你留心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是一个如此庞大、卑微、被忽视的群体。张小曼等人的出现,填补了社会职能的空白。他们取代了社会记者,用个人视角和非虚构文学形式,试图还原自己的所见所闻,还原一个“较低”的维度,并为这一些平时不说话的群体提供依据。出很多表现出近乎本土的风格。
四
鲁迅晚年旅居上海。尽管上海出版业繁荣,他有能力支付稿件,但他常常为局促、喧闹的生活所困扰。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到,隔壁楼打麻将的声音干扰了他的写作。他写下《阿金》等作品,记录自己被“老百姓”骚扰而无可奈何的生活。当他因咳嗽而无法安然入睡时,他希望与熟睡的妻儿一起写出《这也是生活》时,文豪与普通人之间的界限似乎被抹去了,尽管这可能是一厢情愿。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幻想。
当然,在一个成熟的社会,我们应该鼓励劳动者为自己说话。与其抱怨以电视剧为代表的文化产品对现实生活的虚假和不合理的表述,不如说出自己的感受,写下自己的感受。
谁来讲述工人/普通人的故事、向后兼容的客观难度、长期无法体验的一线经验……大量具有专业背景的作者被排除在外。这确实涉及到写作道德的问题。作家还能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完成虚构任务吗?或者这只是一种幻觉?这是桓彦、张小曼向传统文坛提出的问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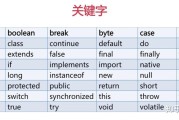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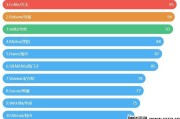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