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珂×子涵蕊啪啪布立刻傲福胆撕聚裂展演回顾:为什么传统剧场看不到这样的剧目?


小珂与子涵,《蕊啪啪布立刻傲福胆撕》(即《共和国之舞》),有剧照留存。该作品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第二届“聚裂”展演中展出,演出时间是 2016 年 11 月 26 日至 27 日,摄影者为黄志豪。
为什么我们在传统剧场看不到这样的剧目?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第二届“聚裂”展演回顾
策划 | 张渊
“聚”和“裂”是所有能量的产生途径,同时也体现在艺术理念和方法的形成与突变方面。从原子层面到宇宙层面,“聚”和“裂”既可能呈现为一个持续的过程,也可能只是短暂的瞬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所发起的一年一度的“聚裂”展演,关注的是动态的发生情况,所指向的是一切具有时间性的事物,强调的是关于经验和体验的表演。其英文译名“ReActor”的意思是,“聚裂”将会鼓励对行动和表演进行重新诠释。
并且会对部分剧目的主创者进行访谈汉斯 - 格奥尔格·克诺普以及撰稿人王霁青会在此处,分别向大家讲述他们对孙晓星所著《这是你要的那条信息……不要让别人看到;-)》以及小珂 × 子涵创作的《蕊啪啪布立刻傲福胆撕》这两部剧的赞赏之处。
阴森的“萌物”?——剧场里的二次元
文 | 王霁青(柏林自由大学,戏剧舞蹈学)
女孩不停地梳理着黑色翅膀上的羽毛。在《这是你要的那条信息……不要让别人看到;-)》的演出进行到约三分之二的时候,她最终再次背上道具,离开了那个格子空间,也就是宿舍的床铺。那个格子空间虽然让她的行动受到限制,无法舒展,但只要借助电脑屏幕的一点儿微光,她就能在其中怡然自得。上一次出游是因为饥饿的冲动,那是遗存的动物本能在起作用,同时突然被激活的猎人嗅觉也帮了她,让她在半径五米的现实世界中找到了肉身消耗的补偿。这一次,她大概是受到了想象世界的驱使,变身为仿佛能够通达灵体的异能者,铺开一地蜡烛,想要在阴阳两界之间用火光为逝者指引路途。

孙晓星创作了《这是你要的那条信息……不要让别人看到;-)》,有其剧照。该作品在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第二届“聚裂”展演中展出,演出时间是 2016 年 12 月 3—4 日,摄影由黄志豪完成。
诡异之处在于,蜡烛有着包裹着电池芯的塑料壳,并且烛光并非通过用火点燃而产生。她仅仅只需按下通电的按钮,这种快捷的操作就驱散了“灵韵”。那是本雅明所描绘的“空间与时间构成的一种奇异织体”,其来源是遥不可及的远方。它原本是不可以被触碰的,然而能够通过呼吸来显现,借助身体的感知力,从远处逐渐靠近。它会在“夏日午后,借助地平线上的一道山峦或者一道树荫,将它的阴影投射在休憩者身上”。
机械复制时代,人们的感知会持续被打断,目光会时常转移到契合的缝隙上。例如,在当晚的剧场里,我的目光就不自觉地落在了塑料上。这种难以降解却又被大量制造和组合利用的廉价材料,假冒圣物,打破了传统符号的秩序,在切断旧日等级的链条之后,又把我们拉入了某种新的复制循环。材料以伪劣、平庸的面目出现时,会让人有这样的感受。女孩的宿舍“礼仪”不仅没有展现出应有的规范,反而附带着对自身行动的嘲讽。它提醒人们,不要凝神静观,不要沉浸在单一、完整、不可逾越的能指坐标系之中,不要专注忘我地去感动。走神和出戏,在现代人的观看过程中是不可避免会出现的。它们能护送我们进入间离模式,让我们认识到,虚假不仅存在于材料的劣质和模仿的笨拙方面,还体现在如今行事方式早已偏离古礼语境,但仍对本真性有着像教义般的维护。

孙晓星创作了《这是你要的那条信息……不要让别人看到;-)》,有其剧照。该作品在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第二届“聚裂”展演中,演出时间是 2016 年 12 月 3—4 日,摄影由陈井年完成。
后来,女孩与坐在舞台上的我有了一次接触。她用软濡的声音先问道,我们会不会把她看作离奇古怪的人。接着,她告诫我别食用另一位走近观众的女孩带来的食物。最后,她嘟囔着“我是天使”,戴着翅膀在人群中离去,脚步有些跌跌撞撞。我注意到她的装扮:有一条及膝的连衣裙,领口以及袖口都镶着蕾丝边,还有长长的刘海。这所有惹人怜爱的“萌”元素,从第一眼望去的感觉来看,似乎与“离奇古怪”有着很大的距离。然而,在那清纯少女形象的背后,却隐藏着让人感到不安的倒错。日本的“萝莉”文化,通过二次元动漫和游戏进行传播。在其影响逐渐扩大的过程中,重新对生活中的女孩进行了定位与塑造。使她们迎合社会对女性保持“幼齿”状态的某种期待,并把这种期待视为理所当然。在这样的对象化过程里,一种古老的焦虑被唤起:文化制品原本是为人类制作的,如今却将人变成了玩偶。图像逆袭成为了人的造物主。

孙晓星,《这是你要的那条信息……不要让别人看到;-)》,剧照,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第二届 “聚裂” 展演,演出时间:2016 年 12 月 3—4 日,摄影:黄志豪
在人、偶难以分辨的模糊状态里,“萌物”给人带来了阴森的感觉。这一母题在德国浪漫派的小说中早已有所体现:一方面人们对机械装置极为着迷,另一方面又对其不信任,担心它会具备和人一样的自我意识。霍夫曼的恐怖小说《沙人》为技术披上了神秘巫术的外衣,从而增强了那种不确定感。主人公纳撒内尔童年时的梦魇,就是传说中促使孩子入眠的沙人。沙人有着吸引眼球的魔力。纳撒内尔长大后,仪表商人向他推销一种被延长的“眼睛”即望远镜,这激发了他的疯癫。当他得知,可爱的、让他倾心的奥林匹亚(作者借这个名字对古典主义进行了恶搞)实际上只是没有生命的机械人时,幻象中燃起了火焰。在圣经的视像里,火的眼睛本是灵魂之眼(可参考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在此,它成为了一把双刃剑,使得纳撒内尔在那破损的自恋倒影里(就像机械娃娃一样)被灵魂所纠缠。当晚观剧时,我确实在舞台的布景中看到了变了调性的“萌物”道具。那是一串眼球,悬挂在鼓手和吉他手的床铺前方。每当音乐响起,那重复的鼓点以及鬼祟的曲调都让人感到毛骨悚然。这样的视音搭配似乎在暗示:阴森,而这种阴森就是“萌”在曲面镜中所产生的反射。
我们来考察这位动摇信仰的恶魔,即复制性。机械复制与之相比,受数字代码支配的仿真让那些在网络中漂浮的符号更显抽象。这些符号早已脱离与真实世界的关联,背叛了代理现实的作用,在庞大的数据库生长系统中进行搭配重组,从而构建出虚拟的现实。东浩纪在《动物化的后现代》一书中分析“萌”要素时曾写道。
“御宅族”系文化的特征是人物“萌”。这并非仅仅是“御宅族”们自身深信的单纯感情投入,而是在角色(拟像)与“萌”要素(数据库)的双层构造间往返,这是极为出色的后现代化消费行动。在“御宅族”们喜欢特定人物的消费行动中,还隐藏着奇妙且冷静的另一面。他们盲目地投入,然后分解对象的萌要素,接着在数据库里进行相对化。

孙晓星,《这是你要的那条信息……不要让别人看到;-)》,剧照,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第二届 “聚裂” 展演,演出时间:2016 年 12 月 3—4 日,摄影:黄志豪
回到剧场。虚拟世界很强大,我们能否依靠剧场中身体的在场性(Präsenz)来抵抗世界的偶像化呢?当得知身体本身是在区分组合原则上架构起来的符号时,会不会有些失望?借用剧场学家 Hans-Thies Lehmann 最近一次讲座的题目“剧场:一个吞噬媒体的机器”。狼吞虎咽般地纳取食物并为我所用叫做吞噬(fressen)。剧场,这看似沉沉老去的旧媒体,完全能够借助新媒体来重新武装自己并且重新认识自身。
如果有人在寻找 “人民的艺术”……
文由汉斯 - 格奥尔格·克诺普所著,他是“聚裂”展演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曾担任欧盟国家文化协会主席以及德国歌德学院总秘书长。
翻译 |谭昉莹
中国人对“身体意识”好像不是很敏感,然而在欧洲这方面至少已经很普遍了。触摸、舞蹈、摆动,凭借身体的运动单纯地享受乐趣,以及与人交流,这些在欧洲人看来似乎都和中国人不相关。
如今到中国旅游的外国人会感到惊讶,无论去到何种规模的城市,晚间的城市公共空间都有一群以女性为主的中年人聚集。她们有规律地舞动着,沉醉其中直到深夜。在这些地方,不管聚集的人群数量多少,哪怕独自一人,也都会跟着不同的音乐和节拍跳舞。
这类似于欧洲人时常提及的“公共空间”,无论贫富差异,无论阶级差别,任何人都能够使用这块区域。它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是属于人民的。
这群人里,有人负责把音响带来,然后播放中国或者国外的音乐,只要有节拍就行;有人负责领舞,其余人在后面结对或者独自跟着跳。他们的舞步都很标准化,能看出有些人受过良好的相关训练,而更多的人只是跟着身体扭动。我走在上海街头时,在小花园或者大型广场上都能看到正在跳舞的人和在一旁围观的人,他们都很享受其中。我也乐于看着这一群人。

小珂与子涵,参演《蕊啪啪布立刻傲福胆撕》(Republic of Dance),这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第二届“聚裂”展演的剧照。演出时间在 2016 年 11 月 26 日至 27 日,摄影者为沈逸。
在一些偏远省份的小镇上,这样的景象依然不断。这种群体活动究竟源自何处?是谁在组织?是谁在发起?第一个跳舞的人是谁?他们从哪里学会的舞?这对人们意味着什么?这是一场美妙且极其随性的聚会啊!
我时常在问自己,能否将这种“广场舞”融入到一段编舞里。我认为如果真这么做,或许会有一些未曾经历过或想象过的结果:会有纯粹的身体的喜悦感,会有从这些普通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快乐,身体会成为另一种语言,进而成为沟通的工具。我觉得这如同中国的戏曲一般,每一个动作都蕴含着别样的语言。那些跳着舞的人,定然比那些时常前往戏院的资深戏迷更加懂得这门艺术。他们或许也未曾受到过多廉价大众娱乐的“侵害”,因为那样的全球性节目并不能让所有人都成为积极且富有创意的人类,而仅仅能让他们成为被动的观看者。这是一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的现象。然而,我在这里至少看到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东西。并且,这些普通人都对它有很好的掌握。
当我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看到《蕊啪啪布立刻傲福胆撕》(其英文标题“Republic of Dance”的中文读音,意为“舞蹈共和”)的表演时,我感到十分高兴,并且还有些惊讶。实际上,这个活动呈现的就是一种“共和”(republic)的概念,它是由拉丁文“Res Publica”演变而来的。现在,“公共事件”来到了舞台之上。不管参与这场表演的人数是多少,关键在于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在其中找到了归属感。
这场演出引出了我之前对群众广场舞的所有疑问,在舞台上还抛出了更多新问题。广场舞的形式反映了人们内心的生活,尤其对于中年女性。她们的期盼、悲伤、感激和挫败感,都通过舞蹈展现出来。舞台上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生活,能够打动人。一位女性说:“我跳舞时,会忘掉自己的孤独和悲伤。”这一幕深深印在我脑海里。艺术的意义难道不就在于此吗?从舞蹈编排方面来看,将专业舞者和纯粹喜欢跳舞的普通人混合在一起进行编排,是一个很棒的创作。

小珂与子涵,参演《蕊啪啪布立刻傲福胆撕》(Republic of Dance),有剧照。该作品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第二届“聚裂”展演中,演出时间是 2016 年 11 月 26 日至 27 日,摄影者为黄志豪。
我在表演中看到了一些极有天赋的舞者,我得说他们是真正的艺术家。若有人在寻觅所谓的“人民的艺术”,那就看看这里吧,每个人都能成为艺术家。它无需他人来告知大家什么是艺术,也无需告知大家如何去创作或看待艺术。这是群众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人民的艺术”。
他们以相同形式表演,但能看到每个人的不同特性。这场编舞中,融入了每个人讲述自己故事、生活经历、梦想、希冀和期盼的表演。我一直被震惊和感动,希望能加入他们。我自己似乎很少经历过通过身体运动来展现生命喜悦的事情。
每个表演者,那些真实存在却未具名的人,从台后依次走出并来到光亮处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被赋予了个性,成为了鲜明的个体,而非仅仅是一大群在舞动的人。同时,这样的舞蹈与我们在大剧院看“芭蕾”时所说的舞蹈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源于欧洲的封建社会,之后逐渐被中产阶级人士所喜爱,然而到了如今好像已经丧失了之前的地位。

小珂×子涵,《蕊啪啪布立刻傲福胆撕》(Xiaoke and Zihan, Republic of Dance),剧照,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第二届“聚裂”展演,演出时间: 2016 年 11 月 26 — 27 日,摄影:黄志豪
在搜索新的艺术形式时,《蕊啪啪布立刻傲福胆撕》这场演出绝对值得深入研究。从总体来看,其表演所选取的题材都能够被当代观众理解和欣赏,并且这些表演也是为当代观众而呈现的。
表演的指导和演出,一方面在对一些问题作出回答,另一方面也在对我们今天的世界提出问题。艺术家应当是个研究者,去研究我们所经历的这些生活、世界和命运,它们是如何被人们赋予文字、声音和图像的。这些生活、世界和命运处于瞬息万变的状态。
所以,艺术家像其他研究者一样,需要空间来形成全新的、或许有些激进的表达形式。一开始,这种形式只会受到一小部分人的青睐。在研究和处理这些问题时,同样也需要这样的空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就是很好的这种存在,而这些地方需要为这样的创造性提供发声的机会。这样的研究不管发生在哪里,那里就会有新的创造出现。
从欧洲人的视角来看,《蕊啪啪布立刻傲福胆撕》向我展现了中国普通群众的内心世界,包括他们的美、他们的梦、他们的期待以及他们的悲伤,这些其实就是生活本身。它使得这些广场舞舞者与其他人之间的距离更近了。
编辑 / Art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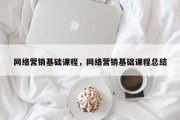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