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关键词 (文学理论关键词分析)
本文目录导航:
文学理论关键词——文化霸权(Hegemony)
在文学理论的词汇库中,文化霸权(Hegemony)这一概念如同一把钥匙,揭示了权力与意识形态的深层互动。
其词源可追溯至古希腊的“ege-mon”与拉丁文的“egemonia”,最初是指外来统治者的统治,但在19世纪,它扩展为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的广泛政治控制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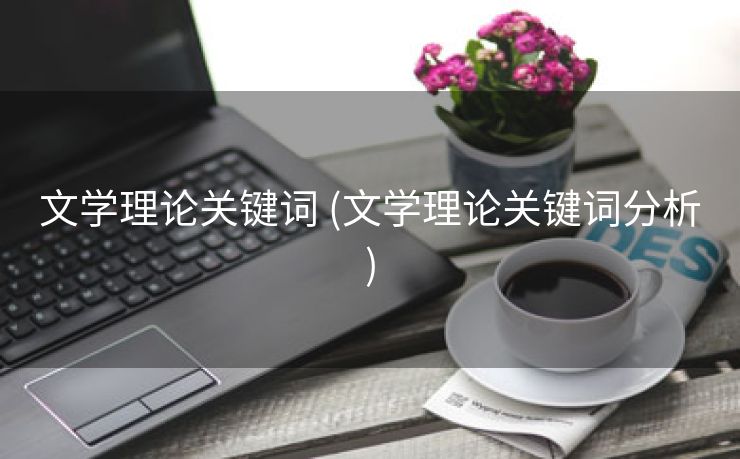
雷蒙德·威廉斯在《关键词》中,以深入的词源学分析,揭示了文化霸权概念的演变。
他指出,这个词在葛兰西(Gramsci)的理论中获得了新的内涵,不再仅限于直接的政治管辖,而是涵盖了对社会观、人性理解和关系模式的普遍支配,使其渗透至大众意识,成为被接受的“常态”和“常识”。
文化霸权的起点可追溯至普列汉诺夫1883-1884年的观点,作为无产阶级推翻沙皇制度策略的一部分,强调了文化领导权在阶级联合中的核心作用。
列宁在《怎么办?》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更是强调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角色,既要通过宣传参与大众,又不能放弃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这为文化霸权概念的深化提供了重要视角。
然而,真正将文化霸权理论化并赋予其深刻影响力的,无疑是葛兰西。
在《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中,他首次明确使用“文化霸权”这一术语,区分了统治与领导的区别,强调了通过大众同意实现的统治方式。
在《狱中札记》和书信中,他进一步阐述了文化霸权的动态平衡,即统治者在掌握政权的同时,必须通过文化领导来争取并维持大众的认同。
葛兰西的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霸权不再依赖暴力,而是通过媒体、教育等手段,通过道德和精神领导地位,使人们接受其统治理念。
这种统治并非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是统治与反抗之间的持续协商与平衡。
统治阶级通过经济合作和精神引导,逐步赢得大众的认同,形成暂时的社会经济和精神一致性。
文化霸权并非与经济基础脱钩,而是建立在经济活动的核心职能上,是全面统治的体现。
葛兰西强调,知识分子,尤其是“有机知识分子”,在领导权争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作为中介,推动着社会的变迁和大众文化领域的深化。
对于大众文化,葛兰西的理论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视角,既非单纯的消极影响,也非盲目推崇,而是将其视为意识形态斗争的舞台,国家与大众的互动和协商之地。
在多元化的斗争形式中,如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等,文化霸权的斗争形式更加丰富,但必须警惕过度泛化的观点,它不应掩盖阶级斗争的现实。
总的来说,文化霸权是权力、意识形态和经济相互交织的复杂现象,它的存在与演变,为我们理解社会结构、文化变迁以及大众文化的复杂性提供了深刻的分析工具。
通过深入研究文化霸权,我们得以更全面地审视现代社会的权力动态和文化斗争的多元维度。
文学理论关键词——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
存在主义,作为20世纪影响最深远的哲学思潮,不仅在学术和思想层面,而且在大众文化领域都占有显著地位,堪称时代精神的缩影。
此思潮萌芽于19世纪末,但正式以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为标志,在法国流行开来。
尽管名为“存在主义”,实际上更应称为“生存主义”,因为最初概念是由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提出的,意在描述人的生存状态。
米兰·昆德拉在他的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使用了“生命”一词,更贴切地表达了克尔凯郭尔的原意。
而“存在”一词,无论在西方哲学还是中国思想中,都是核心概念,相当于“道”,象征着是、有、在(或存在)的三位一体。
“生存”一词,原本在中世纪用来表示“存在”,后来特指“人的存在”或“生存”。
而在古典思想中,上帝被尊为“最高存在”,标志着其独一无二的地位。
黑格尔《逻辑学》探讨从“存在”到“最高存在”的进阶,最终指向了上帝。
存在主义的核心在于探讨在一个失去根基、被虚无主义笼罩的时代中,个体生存的状况与自由。
这一主题与现代派文学和基督教思想密切相关,因此,存在主义哲学与存在主义文学、基督教存在主义紧密相连。
第一个存在主义思想家也是基督教存在主义者,克尔凯郭尔对人在极端情境下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入分析,奠定了存在主义的基本原则。
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和舍斯托夫深受克尔凯郭尔影响,批判理性主义。
马利坦的存在主义则更多融入了“新托马斯主义”,而马塞尔则是法国最早的基督教存在主义者。
除上述基督教存在主义者外,尼采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其生命、本能、权力意志等概念,以及“超人”形象,都为存在主义提供了思想资源。
真正意义上的存在主义创始人是海德格尔,他将尼采的语言转化为纯粹的哲学语言,探讨了存在主义的核心。
尽管海德格尔晚年对存在主义持怀疑态度,转向对真理和存在的历史性的探索,但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整个时代。
法国存在主义者萨特、波伏娃和梅洛·庞蒂等人的贡献不容忽视,他们的存在主义哲学在文学、哲学、神学和心理分析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
存在主义不仅仅局限于哲学领域,它还影响了文学、神学和心理分析,成为现代人思考生存意义、自由意志和伦理责任的重要框架。
在虚无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存在主义代表了个体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追问和对生存意义的探索,是20世纪文化精神的典型体现。
文学理论关键词——第三空间(Third Space)
“第三空间”这一概念直接源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列斐伏尔()。
这位漂泊的知识分子深刻领悟了人类存在的空间性、历史性和社会性,并创造了一套贯通现代世界复杂情境的研究方法,在跨学科立场上把握日常生活和空间生产的辩证法。
列斐伏尔有一个精彩的比喻:人生在世,恰如“蜘蛛”结网。
“蜘蛛网”就是这个复杂、流动的创造性空间的隐喻。
空间,作为真实与想象的混合物,具有一种亦此亦彼的开放性,生成于一种永无完结的过程之中。
索亚的“第三空间”就是这种开放性和创造性的空间,揭示了历史地发生转换和社会地展开建构的环境:开放的空间,一个理想自由的交流环境,以及一个无法穿越的迷宫。
索亚引用博尔赫斯的《阿莱夫》(The Aleph)将“第三空间”形象化:“空间之中一个包罗万象的点”,“在那独一无二的巨大的瞬间,我看到了无数可爱又可怕的场面”,“目睹到了那个秘密的、假想的事物……它就是无法想象的宇宙”。
这一空间是对真实空间和想象空间的解构和重构,它呈现的是一种重新认识空间和再度呈现空间的可能性。
美国学者爱德华·W.索亚(Edward W. Soja)提出“第三空间”并运用,是一个重要跨学科批评概念。
首先,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种变革性方法,“第三空间”激励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空间意义。
其次,作为一种后现代文化政治的理论与实践,“第三空间”体现了后殖民主义对文化帝国意识形态的抵抗,女性主义对父权中心主义传统的颠覆。
最后,作为一种哲学思考向度,“第三空间”代表着当代思想对传统空间观念及其蕴含的思想方式的质疑。
空间性和人类的存在与生俱来。
尤其在当今世界,人类生活的空间维度深深地关系着实践与政治。
但空间是真实的存在,还是想象的建构?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自然,还是文化?在过去的若干个世纪,人类的认识徘徊在二元论的思维模式之中,试图在真实与想象、主观与客观、以及自然与文化之间给空间性定位。
由此便出现了两种空间认识模式:“第一空间”的透视法和认识论模式,关注的主要是空间形式之具体形象的物质性,以及可以根据经验来描述的事物;质性,以及可以根据经验来描述的事物;“第二空间”是感受和建构的认识模式,它是在空间的观念之中构想出来的,缘于人类的精神活动,并再现了认识形式之中人类对于空间性的探索与反思。
如果可以把“第一空间”称之为“真实的地方”,把“第二空间”称之为“想象的地方”,那么,“第三空间”就是在真实和想象之外,又融构了真实和想象的“差异空间”,一种“第三化”以及“他者化”的空间。
或者说,“第三空间”是一种灵活地呈现空间的策略,一种超越传统二元论认识空间的可能性。
随着全球时代的到来和都市危机的加剧,这两种认识空间的模式就暴露出其自身的局限性,“空间意识的他者形式”也开始涌现。
人们面对着现代媒介所建构出来的虚幻形象,日常生活和电子传媒之间存在着无法和解的爱恨情仇,一切政治策略穷于应付日益增长的贫困、愈演愈烈的种族歧视以及空前恶化的环境,不可和解的文化冲突导致了暴力、犯罪与战争。
那些既非真实也非想象的地方,那些既非经验亦非先验的空间,那些幽灵一般游离于自然与文化之外的空间,就是“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认识模式所无法把握的空间。
这种“测不准的空间”,不仅意味着地点、方位、景观、环境、家园、城市、领土等等,其边界不断漂移和外观不断变化,而且意味着与它们相关的一系列概念都具有深刻的历史社会内涵,并随着文化背景的移易而不断地改变意义。
索亚提出“第三空间”的基本宗旨,就是超越真实与想象的二元对立,把空间把握为一种差异的综合体,一种随着文化历史语境的变化而改变着外观和意义的“复杂关联域”。
“第三空间”概念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福柯。
在索亚看来,以“1968年5月”为象征的西方文化危机之中,列斐伏尔和福柯平行地发现了“第三空间”,不过二者一隐一显。
列斐伏尔正面地大写“他者”,提出了“空间”的差异性;福柯则是将“他者的空间”隐秘铭刻于他的著作之中,长期不为人注重。
福柯以一种“第三化”来开始自己的探索,对二元论空间想象进行无情批判,把人们引向“他者”,建构出“异型地志学”。
这种空间之所以是“异型”的,是因为其中充塞着权力、知识与性欲。
在重新定位种族性、时间性和现代性的过程之中,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也着重阐发了“第三空间”概念。
他的策略,是背靠文化差异,将自己放置在具有差异性的界限位置。
从文化差异书写之中,巴巴引出了“杂交性”(hybridity),并将它放置在“作为他者的第三化范型”之中。
以此“杂交性”筑构起反抗本质主义、解构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挑战单一现代性话语的“第三空间”。
“第三空间”之存在,既非内在,亦非外在,既非殖民世界,亦非被殖民的世界,而是一个比内在/外在、殖民/非殖民二元对立范畴更古老的本源,一些与人类存在共命的认知世界的可能性。
沉入对“第三空间”的探索,即可规避极端主义的政治,而将后殖民世界表现为一个弱势声音的世界。
当代女性主义的迅猛崛起,不仅深化了对空间差异之构成的探索,而且还增强了“第三空间”的开放性。
女性主义不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它往往体现为一些女性文化批评家身体力行的实践,她们的实践突入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空间领域,想象以及开拓差异的空间,从而直白地将自己的“创生性空间想象”移植到充满反抗色彩的后现代文化政治之中。
女性主义开拓的“第三空间”,在父权主义空间、都市主义空间以及现代主义空间之外敞开。
与完整和谐的空间想象相对,女性主义的“第三空间”支离破碎、飘逸不定,但因它属于“他者”,因它具有绝对开放性,而蕴含着生生不息的建设性潜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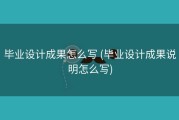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