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大 V 许豪杰被指恋童癖,儿童色情评判标准引争议
写一下这个事件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近日,微博名人、“创业名人”徐浩杰卷入“恋童癖”指控,引发巨大争议。在他被指控开设的“翔太天国”网站中,那些视频和照片算不算色情照片?不少人认为是“打边球”,显得含糊其辞。不止一人表示,看完后并没有发现淫秽或大规模,大概很难判定是传播淫秽物品。即便截图下的一些评论很露骨,但仅凭网络上的照片和挑衅性语言,确实很难说其构成猥亵儿童罪。(见爆料人@沉默如海的最新帖子,点击进入查看)

是不是真的?
其实,很多网友只是混淆了,儿童色情和成人色情的评判标准完全不一样,严格意义上来说,恋童癖和儿童色情爱好者(传播、观看、买卖、持有)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如何判断是否是儿童色情?儿童色情为什么要受到严惩?如果“恋童癖”或者儿童色情爱好者只是在网上看看照片、看视频,产生性幻想,为什么要受到谴责?恋童癖到底是什么?
由于恋童癖和儿童色情,尤其是对男童的性侵犯,目前在国内从法律层面到公开讨论和普及都很欠缺,所以我写了一篇简短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儿童色情制品的定义与区分
儿童应该受到社会特殊保护和对待的想法其实是很新近的事情。很多与儿童权利和儿童福利相关的概念和法律措施都是在上个世纪随着工业的发展、民权运动的兴起和女性地位的提高才逐渐成为共识。毕竟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之后,儿童被认为是战争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今天,当我们在中国讨论儿童保护问题时,几乎总是不得不提到一份权威的国际文件——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这是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人权文件,具体规定了儿童的广泛权利。中国是该条约约200个缔约国中最早加入的国家之一,也是该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之一。由于各国规定有所不同,而儿童保护力度强大的美国并未加入该条约,《儿童权利公约》便成为我国语境中讨论和引用儿童性虐待/儿童色情问题时的重要参考。
《儿童权利公约》第34条意义重大,除了明确规定缔约国有义务禁止一切形式的针对儿童的性虐待(又译“性虐待”)外,还提到还应禁止对儿童的性剥削。这一首次提出的新概念,不仅指“引诱或强迫儿童卖淫/从事非法性行为”,还明确指向儿童色情,即“利用儿童进行淫秽表演/利用儿童作为淫秽对象”。
什么是儿童色情制品?它是“以任何方式展示儿童从事真实或模拟的性行为,或主要为了色情目的展示儿童性器官的任何材料。”(《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按照这个定义,当年被封的“多彩童年”百度贴吧,含有大量儿童色情图片。
即便是在输出“正太/萝莉控”一词的日本,对“儿童色情”依然有明确的定义,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色情分级标准,比刑法中对“猥亵罪”的定义要清晰得多(刘建立,2014)。儿童模仿或类似性行为(甚至儿童之间的性游戏)、儿童抚摸或被抚摸性器官、儿童不穿或只穿少量能引起性欲的衣服的照片和视频,都被视为儿童色情,仅仅提供这些就可能招致刑事起诉和罚款。
受《儿童权利公约》的影响,日本于1999年颁布了《儿童卖淫及儿童色情制品处罚法》,其中第2条第3款规定:
“儿童色情制品是指以允许视觉识别的方式记录下列儿童图像的照片、电磁记录或其他媒体:
a.与儿童或儿童之间发生性交或类似于性交的行为有关的儿童行为形式;b.与他人触碰儿童性器官或儿童触碰他人性器官有关的儿童行为形式,可满足或刺激性欲;c.儿童赤身裸体或穿着极少衣服的行为形式,可满足或刺激性欲。

既然叫做Shota Paradise,那我们就来看看日本的儿童色情法律是如何定义和规范的吧。
由于我国没有单独立法,一般依据是刑法中的“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其中也包括禁止儿童色情的内容。虽然2010年就发布了关于涉及14岁以下儿童的互联网内容传播的司法解释,但两高院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均未对“淫秽”作出解释,任由行政、司法机关自行裁量。一些网民经常对这一点感到困惑,到底要露骨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淫秽?这些边缘图片很难达到淫秽的标准吗?
产生这种混乱的原因是,目前国家还没有对成年人和未成年人色情制品的分类。
以分级制度相对完善的美国为例,或许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为何儿童色情与成人色情的评判标准不同。
早在1957年,美国就在塞缪尔·罗斯案中确立了“罗斯标准”,历史上对色情制品的标准进行了划分:分为淫秽内容与不雅内容,俗称硬色情与软色情的区分;如果内容稍微带有一点色情,就是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否则《金瓶梅》也会作为淫秽书籍被禁;极其露骨的色情内容则不受保护。

罗斯标准,6名大法官同意,3名大法官反对(图片来自)
该标准虽然简单,但在实践中却极其不明确。由于不区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颇有些像当今中国的情况,即当时一些保守的州在执法上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以“对未成年人有害”为由禁止那些成年人完全可以接受、无害的色情材料。尽管不断修改,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始终未能就淫秽材料的标准达成共识。在1958年的“跨大陆电路有限公司诉达拉斯案”中,哈伦大法官感叹,在13起淫秽材料案件中,大法官之间竟有55种不同意见,“这是任何其他宪法判决都难以比拟的”。
最后,在1973年的色情作品经销商米勒诉加利福尼亚州一案中,最高法院确立了判定硬色情的“米勒标准”,即:1、当代社会标准:作品整体上所表达的内容是否对普通人具有性刺激;2、作品对性行为的描绘或描述方式是否明显具有冒犯性;3、作品整体上是否具有文学/艺术/政治/科学价值(艺术作品是否会被认定为色情作品也是一个考量标准)。

米勒标准,5 名法官同意,4 名反对
这三项标准也被称为“三叉戟标准”,至今仍未改变——除了儿童色情内容。
米勒标准之后,新的问题很快出现。色情材料为了寻求合法性,开始在第三标准的“文学性、艺术性和科学性”方面下功夫。随着20世纪70年代色情电影、色情小说、色情杂志甚至裸体跳舞合法化,色情产业不断挑战所谓“硬色情”的底线,把儿童色情作为争夺市场的制高点,儿童成为色情材料的道具。那是1977年,大多数州还没有意识到儿童色情的危害。
最后,在1982年的费伯案中,最高法院判决米勒标准不再适用于儿童色情的判定。该标准对于任何涉及儿童的色情材料都会更加严格。即使有文学和艺术价值(米勒标准第3条),它仍然逃脱不了犯罪,也不受宪法言论自由的保护。换言之,软色情仍然会被判定为儿童色情。判决书原文为:“儿童色情并不要求限制的物品是淫秽材料。”(Neil C. Blond,《布朗德宪法》,纽约,1993,第34-341页)

九位大法官一致同意 Fobo 标准
此案引发了次年的《儿童色情法案》。基于对儿童被用作色情道具的憎恶和对保护儿童的共同关切,众议院以400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该法案。法案规定,任何人制作、贩卖或持有儿童色情制品,将被处以最低15年监禁和10万美元罚款,最高30年监禁。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对此类犯罪处罚最重的国家之一。
色情行业可以合法,但儿童色情就别想碰了。
美国法典(18:2256)规定:
儿童色情制品是指描述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进行露骨性行为的文字和图片。露骨性行为分为真实性行为和模拟性行为,具体包括:(A)同性或异性之间的任何性交行为,包括生殖器对生殖器、口对生殖器、肛对生殖器或口对肛的性交;(B)兽交;(C)手淫;(D)虐待狂或受虐狂;(E)淫荡地展示生殖器或阴部。
(参见:胡国平,《美国案例:自由挑战道德》,2014年)
到底是不是“淫秽”和是不是“儿童色情”,应该区分开来,出台规定彻底堵住利用儿童玩软色情“边缘球”的可能。比如成年人穿着短裤,翘着屁股做一些性暗示动作的照片,不会被认为是“淫秽”,最多是“低俗”,大概不能被称为色情照片而被禁;但如果照片中是年幼的孩子在做这些事情,即便摄影师努力向艺术摄影靠拢,也可能符合儿童色情的定义而被禁。
在呼吁分类的同时,国内也有学者提出,符合刑法“淫秽罪”标准的儿童色情制品,应当以“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处理;不符合刑法标准的,则应依照《未成年人保护法》或针对未成年人的司法解释处理(参见吴亮,2014;梁鹏、王兆同,2004)。
恋童癖定义:从常见到禁忌

在采访中,故意模糊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界限的色情产品
恋童癖最大的问题,在于其欲望的对象是缺乏足够判断力、性成熟度不高、处于弱势地位的儿童。李银河曾提出“性爱三原则”,即“自愿、成人、私密”,恋童癖显然不符合这一原则。这种成年人与未成年儿童的性关系,明显是不平等的。
恋童癖这种可以称为病理现象的案例并不多,“恋童癖”一词仅用于社会文化意义上,作为精神疾病的一种,恋童癖甚至在学术界也未得到很好的研究。这种广义与狭义的区分,就像中西方文化都把行为异常的人称为“精神病患者”,并不代表这个人就是可以诊断和治疗的精神病患者。
关于恋童癖,学术界存在争议。它到底是性变态/精神障碍,还是性取向?美国精神病学会2013年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中,将恋童癖定义为“性取向”。除非这种恋童癖伤害了孩子,或者使人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否则不能被称为“精神疾病”。这引起了极大的抗议,被理解为恋童癖合法化,最后又改回“性兴趣”。
判定这三种恋童癖到底属于哪一种,就像争论徐浩杰是不是恋童癖一样,并不重要,很多儿童色情制品的传播者和制作者,并不是恋童癖者,而是投机商人。
在人类历史上,成人对儿童的性剥削其实很常见,也并不可耻,可以说东西方都一样。对儿童权利尤其是性权利的保护和重视,是非常近的事情。就连“恋童癖”这个词,也是在1900年以后才出现在英文中。最早的使用,可以追溯到1896年Richard von Krafft-Ebing的德国著作。
如果我们追溯历史,在古希腊,男子与未成年男孩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爱欲),既是学徒又是情人,是肉体与灵魂的结合。正如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所描述的,这种男子与男孩的结合被认为是一种高层次的爱情,高于成年男子之间和成年男女之间的爱情,具有“爱的智慧”的教育目的。这种传统可能很难被今天的人们理解,因为它逐渐偏离了教育功能,成为了成年人对男孩的情色利用。在中世纪的拉丁诗歌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中侍酒的美少年伽倪墨得斯的形象中,都有很多这种关系的表现。基督教对这种事情予以谴责,但力度不如他们禁止手淫那么热烈(Goodrich,1976),更不用说对女童的性侵犯和性剥削了。同样,在中国历史上,对儿童的性剥削和利用也成为一种社会潮流。 妓女既有少女,也有少年(“香姑院”是男妓的妓院)。南北朝梁建文帝萧纲有著名的《爱童子》诗,赞颂“爱童子,字字珠玑”。张岱自称“爱美婢,爱童子”,一般认为这是一种文雅。此外,日本、土耳其、阿拉伯、埃及、非洲等地都有成人利用儿童进行性行为的历史记录(Trumbach,1977)。
这并不意味着恋童癖拥有历史合法性,儿童在历史上被当作宠物、被当作童工、沦为性奴隶,他们或许被珍惜、被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拥有足够的尊严和应有的保护,他们更多时候被视为成年人的附属财产。近百年来恋童癖的建构,源于人权理念下儿童保护意识的兴起:该词最早在1896年德语中使用(paedophilia erotica),被精神病学权威克拉夫特-埃宾用来分析儿童性犯罪的性精神病理学——换句话说,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词理解为专门为了对付那些攻击儿童的变态成年人而创造出来的词汇。
现代社会的趋势是,一方面成年人的性自由越来越大,越来越宽容;另一方面成年人的性行为、对儿童的性剥削越来越被禁止和鄙视。儿童权利的概念在近代被提出,其实就是呼吁“儿童也是人”。
由于恋童癖者往往更喜欢14岁以下的法定年龄、性心理还不够成熟的儿童,因此负面影响会更大。被性侵的愤怒和痛苦也会被投射和释放在他人身上。研究者发现,童年时期遭受过性侵的男性更容易虐待儿童(Bolen,2001;Finkelhor,1984)。或许是因为性别管教教会了女性温顺顺从,童年时期遭受性侵的女性受害者选择将愤怒和自残内化,更容易陷入吸毒、情感自毁等行为(Finkelhor,1984;Russell,1984)。
儿童色情“不算犯罪”吗?
被豆瓣揭发恋童癖的徐浩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豆瓣说徐浩杰是正太控,这根本就不算新闻。”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叫做“正太控”、“萝莉控”,把它降到二次元,然后宣称“性幻想不是罪”呢?
这看上去是虚拟儿童色情的“界线”。但事实上,就连被冠以“正太控”、“CP粉”可爱称号的二次元世界,也从未真正脱离过现实,否则也不会有“合法萝莉/正太”这个概念(那什么是非法萝莉/正太?)。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引发热议的“蕾莉CP”和徐浩杰的网站“正太天堂”与虚拟儿童色情毫无关系:因为出现并涉足其中的儿童,都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孩子。二次元文化对此不负任何责任。
那么恋童癖者收集的儿童色情制品究竟有何用途?难道只是为了关起门来获得性享受吗?在警方和研究人员确认的儿童色情罪犯中,儿童色情制品的用途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见《刑事侦查》第8版,2007年):
1、激发性欲,满足性幻想,带来快感。比如去“正太乐园”买男生原创服饰,就是满足性癖好的一种方式。
2.增加受害儿童的性兴趣。例如,一个抵制性行为或不配合拍摄色情照片的孩子可能会受到吸引,并开始觉得这些行为是可以接受的。
3.恐吓、勒索,如威胁孩子不许泄露秘密、不许听话等。
4、利用孩子的好奇心,引诱他们,并交换信息。
5. 牟利。涉嫌贩卖、传播儿童色情制品的人不一定是恋童癖者,只是投机者。真正的恋童癖者的牟利动机更为复杂。当然,赚钱满足自己的利益是最好的。如果做不到,钱也许无所谓。
中国很多家长,尤其是小男孩的家长,对儿童色情制品缺乏足够的认知和警惕,面对儿童性骚扰、性侵,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儿子就是个孩子,不用担心”,在公共场合暴露孩子身体的行为也非常随意,比如让小男孩穿着开裆裤到处乱跑、在社交网络上晒孩子的裸照等等。
其实,这些按照成人色情标准“绕线”的儿童色情爱好者,他们所交流、传播、幻想的照片、视频,都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个体,是相对脆弱的孩子。你愿意孩子的照片在儿童色情圈里被买卖、被评论、被幻想、被玩弄吗?如果你的孩子长大后,无意间发现自己的照片在网上被视为儿童色情怎么办?更何况,这些儿童色情照片中,很多可能是在拍摄过程中拍下的。这些儿童色情消费者中,有些人真的会采取行动。
这也是为什么在国外,收集、持有儿童色情照片和视频也会被判处重刑的原因。儿童色情从来就不只是一些无害的图片和视频,仅供消费,它的制作过程本身就是对儿童的性侵犯和剥削的过程,尤其是未成年人参与明显的性行为,几乎就是性侵犯的铁证。比如1999年,荷兰破获了欧洲最大的儿童色情案,缴获的数万张照片中,最小的孩子只有18个月,最大的只有9岁,其中还包括强奸的照片。
这些儿童色情照片和视频通过一些隐蔽、隐蔽的渠道,在各类色情狂、恋童癖者之间买卖、评论、幻想、玩弄,甚至被用来性侵伤害其他儿童,并通过色情网站悄悄传播到世界各地。受害者很难辨认出自己照片和视频的制作者和持有者,谁也不知道这些照片何时会浮出水面,被别人无意间认出。这种煎熬和恐惧几乎是日复一日的心理折磨,伴随的伤害很可能持续一生。
例如2014年的帕罗琳案在美国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1990年出生的受害者艾米在八九岁时就被其叔叔性侵并拍照。虽然性侵罪犯已被绳之以法,但2007年,早已走出人生阴影的艾米发现自己童年时期被性侵的照片被全国乃至全球成千上万人传播,她一度精神崩溃。随着照片的传播,艾米无法继续大学学业和生活,医生称对她的心理影响可能会持续一生。不过,2009年,艾米终于找到了一名儿童色情照片收藏者,此人清楚拥有她当年的照片,并已认罪。她将帕罗琳告上法庭,要求赔偿。然而,罪犯收集的150-300张儿童色情照片中,艾米的照片仅占2张。 该案件被层层曝光,震惊了国会、学术界和民众,并最终引发了关于儿童色情受害者赔偿制度的讨论。
目前,即便是虚拟儿童色情,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日本)仍备受争议,儿童色情仍是高压禁区。在备受争议的“蕾莉CP”和徐浩杰被指控运营的网站“翔太天堂”中,其实她们甚至不是二次元的虚拟儿童,而是真真切切的真人儿童。
在已对虚拟儿童色情制品进行立法的英国、美国等国家,对虚拟儿童色情制品的分级标准已细化到有“高度逼真”和“一般逼真”之分,其立法禁止儿童色情制品的支持依据,大致且不完全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预防论:虽然没有真正的儿童受到伤害,但禁止可以防止刺激或鼓励儿童性侵害的行为;2、市场论:即“不买卖就没有伤害”,生产、贩卖、传播和收藏会助长儿童色情制品市场,任由人们伤害儿童牟利;3、“脱敏”风险论:一方面,在习惯了虚拟儿童色情制品之后,似乎社会上很多人对儿童都有一种特殊的偏爱,恋童癖者可以借此证明自己和普通人并无二致。 另一方面,当恋童癖者利用虚拟儿童色情内容对儿童进行训练、引诱时,会放松父母和孩子的心理防御,甚至引发儿童追捧动漫色情文化的从众现象。
可悲的是,徐浩杰事件之后,在儿童色情的讨论中,还是有那么多人缺乏判断力,儿童色情制品的交易和消费如此明目张胆,却有相当一部分网民认为这没什么问题。
最后的想法
各国国情、立法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必须承认,我国虽然没有专门立法,很多立法仅散布在各种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中,但相关法律法规不断更新补充。比如,2006年《未成年人保护法》增加了性侵害内容;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信终端、语音电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互联网传播含有未满十四周岁儿童内容作出规定;2013年,《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出台。 还有一些更前沿的尝试,如2016年在浙江慈溪率先出台的《未成年人性犯罪者信息公开实施办法》,模仿美国对儿童性犯罪者信息进行登记公开的做法,被称为中国的“梅根法案”。
徐浩杰的话题核心在于国家没有区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制定色情分级,导致无法在法律上彻底推翻和严惩此类“恋童癖”行为,也无法更好地保护性心理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免受成年人的色情伤害。同一种形式的性侵犯罪对儿童的影响会更加持久和严重,因此更需要对儿童性侵和儿童色情给予更严厉的惩罚,而不是一刀切。希望我们在谴责、声讨、抒情、批判此类行为之后,不要只是简单粗暴地进行运动式的清理和取缔,让这些风头一过就“恋童癖”改名换姓再来,最终只是让儿童色情问题停滞不前。在打击儿童性侵和性剥削的具体实施上,国际上已经有很多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和思考。 作为《儿童权利公约》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和最早签署国之一,我们有充分理由和信心相信,我国完全有能力在惩治儿童性剥削和性侵犯的立法方面做得更好。

是啊,这种贴吧、微博如果陆续被封,没人受惩罚还有什么意义呢?
豆瓣,请你承受压力!感谢@沉默如海等豆瓣用户为此事做出的努力。
我利用了这么多素材,目的只有一个:想把这个事件中争议的部分说清楚,推动这个事件可能带来的改变。希望你们95创业项目徐浩杰用自己去推动这个领域的立法。
更新:本文将于明天(8月2日)在澎湃新闻上发布!非常感谢编辑。虽然可能有所删改,但如果真要推广,还是需要媒体的参与,扩大影响(请参考嫖娼罪最终废除的讨论与推广)。我就不多说了,谢谢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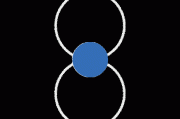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