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大庆石化炼油厂:手套与工作的故事
40年前,我到大庆石化炼油厂工作。当时发行了很多手套,有的是皮质的,有的是一面是皮革一面是帆布的,而且大部分都是白线手套。我在润滑油测试车间工作。这些手套我们干体力活的时候都可以用,但是我们最需要的还是黄色乳胶手套。润滑油是粘稠的,尤其是在冬天。取样时戴上乳胶手套可以防止润滑油渗入手上。这种手套在当时是稀缺商品,球队给了每人一双,我视若珍宝。如今,许多人的厨房里都有这样的手套。当然,它们有更多的颜色和款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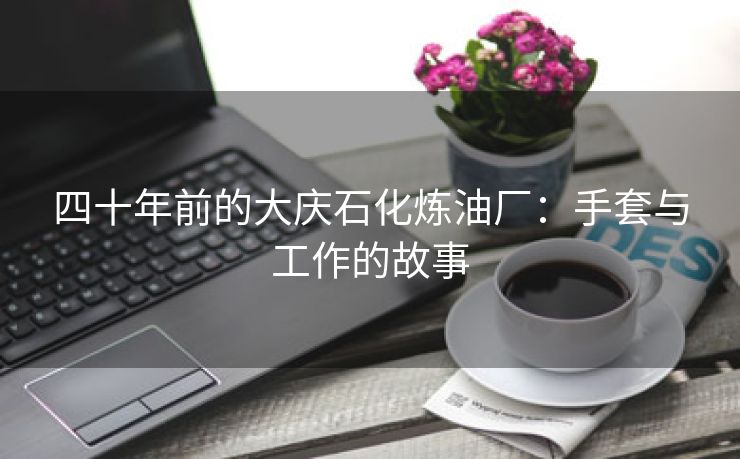
因为经常写新闻稿,我被调到宣传部编辑一份内部“油印”小报,名叫《炼化周刊》。修改、编辑、排版、印刷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印刷这份小报还需要手套。
工厂为宣传部购买了一台高速印刷机。快速打印机与复印机有些相似,但又有些不同。高速印刷机需要蜡纸制版,可以大批量印刷,出纸速度快。印刷前,应将压紧的新闻纸摞松开,以免“卡纸”。为了让这些A3幅面的纸张整齐、宽松,就需要“裱纸”。 “造纸”是一项技术活,如果做得不对,手指或者手腕都会被划伤。纸张的边缘有时看起来像一把锋利的刀片。我多次体会到纸的“力量”。后来,当我开始印刷时,我戴上了一双白手套,它成了我印刷报纸时的必备品。
除了印报纸之外,我每天下午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浏览当天的报纸。我看报纸时通常戴着一双白手套。有人很好奇,问我看报纸为什么要戴手套。我不怕报纸划伤我的手,只是怕我的手指被那些“闻起来像墨水”的报纸染黑。那时候每天都要看很多报纸,美其名曰充电。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黑龙江日报》、《羊城晚报》、《中国石油报》……这些报纸从第1页到第8页,页码12页(有的24页),光是浏览标题就需要一个多小时。我的手指因为阅读而沾上了很多墨水。而且如果戴上手套,手指就不会变黑。
看报纸戴手套常常让我想起一个细节:路遥写《平凡的世界》之前,到图书馆查阅了60、70年代出版的《人民日报》,记录了他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思想是有价值的,并为小说创作的历史背景做好功课。他找了一个多月,由于翻阅报纸的时间较长,他的左手食指和中指指腹都变得很薄,甚至能看到里面的血丝。每当想到这个细节,我的心总是扑通扑通地跳,我会习惯性地看向自己的手指。但事实证明,作家的工作不仅开始于写作过程中,而且还开始于写作之前!
由此我想,如果路遥翻《人民日报》的时候戴上手套,手指不就被磨细了,就不会看到那双布满血丝的快要爆裂的眼睛了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正是因为他没有戴手套,那些布满血丝的手指早已刻在我的记忆里,还伴随着疼痛的痕迹。
现在我们来谈谈袖子。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人都记得,那时候的营业员、会计师、纺织女工,似乎都穿着袖子。铁宁写了一篇文章《怀念孙犁先生》。文章写道,她曾三次去见孙俪先生,每次孙俪先生的手臂上都戴着一对青色的袖子。散文中有很多细腻的描写,比如孙俪先生在花园里弯腰捡黄豆时穿着袖子,或者和保姆一起修补窗户裂缝时。更让笔者印象深刻的是,孙俪先生坐在办公桌前准备写字时,也穿着袖子。由此可见,孙俪先生可能和很多普通工人一样,常年穿袖子。作者用真挚的文字,用袖子描绘出了孙犁先生朴素、真实、清晰的形象。通过细致的描写和情感的表达,孙犁先生执着、坚忍、善良的品格深深地烙印在读者心中。
现在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可能很少听到“袖子”这个词以及这个物体了。如今,炒油条、做包子、煎饼、拉面、炒瓜子等的工人手臂上也出现了袖子,为普通工人轻巧灵巧的动作增添了魅力。为什么它能长久地刻在我的心里,大概是因为它代表着朴素、节俭、纯朴、善良、体贴、温暖……和珍惜。上班时,虽然我在办公桌前写字的时候并没有认真地穿袖子,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每天下午我去一楼收发室取报纸时,那两个女工负责分发报纸期刊的人都穿着彩色或彩色的袖子。蓝色袖子。由此,我也认为袖子与报纸杂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表面上,你戴手套保护双手,戴袖子保护衣服。但如果你体验了戴手套、戴袖子,你的内心一定会变得坚忍甚至无所畏惧。在寒冷多风的冬天,手套和袖套不仅是皮肤和衣服的铠甲,更注入了一种不愿停下来、时刻准备着工作的心情,也蕴含着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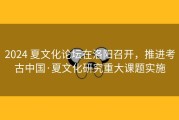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