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二次元与三次元的界限:从凉宫春日的忧郁到现实世界的哲学思考
戴毅
二次元有一个笑话,说在虚构的二次元中寻求三次元真相的人精神有问题。经典情节来自《凉宫春日的忧郁》(见下图,但这并非该剧的初衷)。这个表情包通过建造维度墙隔离了两个世界,满足了二维围合带来的安全感。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西方很多科普、哲学书籍特别喜欢用虚构的故事来举例。科幻和奇幻作品经常是客串。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粉丝群体的壮大,一些二维作品也逐渐出现在专业书籍中。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为什么我们能够理解另一个维度的故事,理解虚构的世界?

这个问题有一个看似简单的解释:因为创作者以现实生活为模板来创作作品,即使是奇幻或虚构的作品,作品本身的逻辑也是自洽的。 2019年,美国物理学家、科普作家丽贝卡·C·汤普森(Rebecca C. Thompson)出版了一本通过《权力的游戏》科普的书《冰、火和物理:科学的科学》(Fire, Ice andPhysics—the science of the science of the science)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刘易斯·托马斯科学写作奖获得者肖恩·卡罗尔在序言中指出:只要虚构作品不是超现实主义的,就一定遵循逻辑,科学家就可以研究虚构的世界。科学精神无处不在,“科学与文学(科幻、奇幻或其他)之间的对话就是文本”,“当我们沉浸在可能性的虚拟世界中时,我们会觉得很有趣,但当我们思考什么时我们以科学的方式看待事物,当我们发现某些东西时,我们会获得额外的享受。”此时,科学成为文学的另一种视角,正如著名物理学家费曼在《发现的乐趣》中描述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区别一样。科学家不仅可以欣赏花朵的美丽。像艺术家一样,还能看到更多的东西:“我会想象花里面的细胞,细胞里复杂的反应也有一种美感。”
但在这个简单的解释背后,还有更本质的哲学原理。不仅如此,它还与古今西方科学史密切相关。那么,让我们从头开始,是的,现在我们要进行一次时间之旅,选择几个关键的时间段进行解读。
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
苏格拉底在与诡辩家的辩论中指出,只有对话才能解开人类的理性。辩证法这个词的词源是对话。今天,马克思主义学者也用辩证法来理解当时的对话,即通过沟通、对话来获取真理。所谓真理,越争论越清楚。在此基础上,他的学生柏拉图将其提炼为一种理解思想世界的思辨方法。 “当一个人不顾感官知觉,试图通过辩证法推理来触及一切事物的本质,并坚持不懈,直到他依靠思想来了解善的本质时,他就达到了可理解事物的顶峰。”柏拉图也说。反思苏格拉底晚年的缺点,认为观念和现象不再是不同时空的感受,观念是永恒的真理,就像他的洞穴比喻一样。本质上,投射只是观察到的现象,既然现象是投射,自然就会产生一定的扭曲或误解,我们只能用辩证法(在柏拉图那里实际上就是哲学本身)来进行归纳分类,将现象构建成一个逻辑体系。他把他的著作称为“拯救现象”,辩证法成为现象的解决方案,由此他提出了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对立统一、矛盾运动、整体决定部分、尤其是他的《巴门尼德》被黑格尔誉为古典辩证法思想的最高峰。
到了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身上,这套方法被他运用到了他理解的方方面面,包括但不限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哲学、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等各个学科。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详细阐述了这一方法。简单来说,保存现象分为三个步骤:(1)找到现象; (2)分析现象,特别是现象引起的矛盾和困难。 ;(3)拯救包含在受人尊敬的思想中的真理。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很多时候,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现象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培根科学传统中的实验现象,而是一种具有经验性质的普遍信念。他说,受人尊敬的概念是一致的,“受人尊敬的概念是指那些被每个人、被大多数人、或者被最聪明的人所接受的概念——也就是被所有人、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或者是一个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概念。”他们中最著名和最受尊敬的人都接受这个想法。”通俗地说,就是拯救常识中含有真理的部分,这种拯救现象的方法也叫辩证法(中国读者都熟悉辩证法,这里就不赘述了,大家只需注意即可。辩证法的内涵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
我们举两个科学和艺术的例子来说明。从科学上来说,当时没有人感受到地球的运动。这是根据当时的经验,大家都认识到的现象。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理论正好可以挽救这种现象。四种元素是土、风、水、火。最重的土会下沉,最轻的空气会向上漂浮,水和火介于两者之间。宇宙是完美的,元素也会回归到完美的状态。该去的地方,宇宙的中心自然是地球,最外层是空气。人的脚底是大地和大地,头顶是天空和空气。毫无疑问,宇宙的中心自然是地球。这就是地心说的起源。它不仅符合当时的观察,而且与亚里士多德的整个逻辑体系完全一致。因此,十多个世纪以来它一直被西方学者所接受和认可。
在艺术方面(包括今天的文学等),我们已经提到了柏拉图的洞穴假说。在柏拉图看来,艺术分为两种,一种是模仿,一种是狂喜。如果是模仿的艺术,既然现象本身就是模仿的幻象,那么在柏拉图看来,艺术和其他虚构就成了幻象中的幻象,显然无法增强人们的新知识。在古希腊,知识和美德的完美是一回事,因此这种作为知识的艺术变得不道德,并可能导致堕落。狂喜的艺术更感性。用尼采后来的话来说,这两种艺术就是阿波罗艺术和酒神艺术。虽然柏拉图晚年稍有放松,但解决这个问题的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模仿的对象要么和我一样,要么比我们好,要么比我们差,并引入了品质。一个人的善恶就是他在道德上的善恶,他可以通过实践来完成符合道德的行为。例如,除了直线运动之外,只有圆形轨道才是完美的;正如上述四种元素在完美状态下运行一样,它是善的、美丽的。对艺术本身的模仿是疯狂的。我们可能会模仿得更好、更差或相同。这样,模仿和狂喜就结合在一起了,艺术通过拯救现象而得到拯救。
哥白尼革命
两朵花盛开,每一朵代表一朵花。按照今天所谓科学的背景,我们已经来到了16世纪。对于这个时期的学者来说,如果继续追随亚里士多德的拯救现象,就会遇到EM罗杰斯的《物理学中的方法、性质和哲学:天文理论(探究物理学)的发展》:“对于古希腊思想来说,对于今天的许多科学思想来说,一个好的理论是一个精确地保留所有现象的简单理论。当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是一个好的理论时,要问“它是否非常简单且易于理解?”以及“它能非常完整地保留这种现象吗?”如果我们再问,‘这是真的吗?’,这不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要求。”
我们都知道奥卡姆剃刀理论(“是不是非常简单易懂?”),也解释了救赎现象(“它能非常完整地保留现象吗?”),那么罗杰斯的意思是什么?一句话是,当时的人们只关注科学理论是否简洁,是否能够拯救现象,而并不关心它是否真实。由此,我们可以重构哥白尼的天文革命,一个与中学课本上完全不同的故事。
对于托勒密这样继承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大师来说,解决问题的核心关键是拯救现象。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太阳和行星在太阳系中的具体位置对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重要的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太阳和行星的轨道必须是完美的圆形。 ,所以他想出了很多本轮和均轮来拟合。例如,今天我们知道火星逆行,因为火星绕太阳的轨道是椭圆形。从地球上看,它的视运动会出现逆行,而托勒密为了挽救这种现象,他的本轮和均轮,用今天的数学术语来说,用许多圆形轨道来拟合成椭圆轨道。这在今天看来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不仅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无法想象,就连很多西方科学家也无法想象。我们稍后会解释这个原因。
古希腊时期,一位名叫阿里斯塔克斯的学者就已经提出了日心说。他的著作并未流传下来,仅在阿基米德的《算沙者》中短暂提及。白尼恰好读过这本书,他的日心说很可能来自阿里斯塔克斯。从数学上来说,日心和地心只是参考系的变化,本质上是等价的。既然是救赎现象,那么做一个数学替换似乎并没有什么影响,但是这个替换本身就会导致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崩溃,因为根据四元素理论,地球显然是在中心;又如日心说会带来地球的自转,因为只有地球的自转我们每个人才能看到太阳和月亮的交替(即“一日”的变化),而根据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物体不具有我们今天所说的惯性。如果地球在自转,那么垂直抛起的物体落下的点显然不在同一个地方,这与大家观察到的不一样,所以地球的自转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科学史学家认为应该把日心说、地心说改为地心说、地心说才能看到如此深刻的变化。
托马斯·库恩将哥白尼革命归因于希腊化天文学传统——拯救现象的传统的复兴,指出哥白尼的物理学除了以地球为中心和地球自转之外,其余都是亚里士多德的。哥白尼专家欧文·金格里奇在《没人读过:追逐尼古拉斯·哥白尼的革命》一书中证明,16世纪的学者长期以来对托勒密体系的不精确和繁琐感到不满。当时的学者早已了解哥白尼的学说,只读过《天体公转论》第一卷是其宇宙论部分。在这一部分中,哥白尼通过将太阳置于中心来挽救了这一现象,受到当时学者的高度赞扬。但大家并不把这个理论当作现实,而是当作数学模型。我们都知道,在《论天球公转》的序言中,有人加了一个歪曲来为哥白尼辩护,说这只是一个数学模型,而不是现实。这种辩护并非出于宗教考虑,而是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发生冲突。事实上,金格里奇在书中证明,虽然《论天球运转》在1616年被罗马教廷查禁,但除意大利外的欧洲其他国家并没有审查这本书,甚至没有被列入西班牙的禁书名单。禁书。这本书。哥白尼的理论之所以能够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发生正面冲突,是由于开普勒的观察,这也是第谷模型得以调和的原因。
此后,牛顿科学革命诞生,现代科学随之诞生,世界再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牛顿革命之后
在进入现代之前,让我们再审视一下救赎现象。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救赎现象,理解其本体论意义,我们会发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虽然都提到了救赎现象,但他们对世界起源的理解是不同的。
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传统源于数字神秘主义,认为数字是世界的起源,物质只是数字的体现。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实体是世界的起源。换句话说,即使他们都相信这种现象是一种幻觉,但投射这种幻觉的原始物体却是不同的。一是道德上的美好数字,二是物质实体。这可以简单理解为柏拉图认为数学更本质、更重要。深奥的东西,亚里士多德认为物理学是更本质、更深刻的东西。哥白尼革命前后,柏拉图主义复兴,我们今天称之为新柏拉图主义。它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做出了一定的和解,因此有学者认为哥白尼实际上是一个新柏拉图主义者,但这并不妨碍他拯救现象。
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主要可以归入形而上学的范畴,即形而上学找到一个第一原理(也称为第一本体论),然后从这个第一原理出发进行推理。当时欧洲大陆出现了以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理性主义者)。他们相信首要原则及其推理是绝对确定且不容置疑的。相比之下,以英国休谟等人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empiricism)则认为形而上学是一种试图理解世界基本结构并同时使这种理解具有确定性的探究。不可能,休谟甚至指出,因果必然性(或因与果之间的必然联系)不是观念关系,因果必然性也不是事实。这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即知识在我们认识世界中的起源和作用。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后,他把这个第一原理归功于上帝,这就是第一推动力的起源。
牛顿革命后,培根式的科学传统开始成为主流,即通过压制自然来揭示真理,实验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对科学家影响很大的康德,他的先验哲学方法也受到了救赎现象的影响。这自然导致大量科学家从传统哲学转向实证主义哲学,实证主义哲学的特点是强调经验,反对思考第一性原理等形而上学问题。我们会发现,这简直就是罗杰斯讨论的翻版。实证主义根本不关心原始问题,也不关心现实是什么。它只关心理论是否简单、优美,实验是否符合理论。至于数学理论是现实还是观察实验是现实,谁在乎呢?你关心吗?下面以霍金和彭罗斯为例。霍金是典型的实证主义者,他的好朋友、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彭罗斯是柏拉图主义者。
彭罗斯在其代表作《通往现实之路:宇宙法则完全指南》(如下图)中修正了柏拉图的理论。该图的意思是,所有的物理世界都受数学世界的规律支配(这些规律只占整个数学世界的一部分)。精神世界以部分物理世界作为物质基础,可以理解整个数学世界。换句话说,没有什么是人类不能理解的。数学规则。该结构类似于埃舍尔的画作,彭罗斯楼梯也由此得名。

这就是彭罗斯和霍金在量子力学本体论上存在根本分歧的原因。一般来说,目前主流的哥本哈根解释并没有给出本体论的解释,而只给出了真实的概率。爱因斯坦、薛定谔等人都不接受这一点,彭罗斯也在其中。霍金更倾向于接受退相干等理论。他甚至接受了人择原理,彭罗斯对此感到困惑,因为它根本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但无论霍金还是彭罗斯仍然是拯救现象,让我们回到亚里士多德的方法。 (1)发现现象:以薛定谔猫为代表的量子力学现象。 (2)分析现象:但分析方法不同:一种选择量子力学的退相干解释;一种选择量子力学的退相干解释;另一个选择广义相对论。 (3)拯救现象:霍金选择的退相干本身就解决了局域化问题,这是目前大多数物理学家所选择的,即使他们不选择退相干解释;彭罗斯选择修改广义相对论来寻找现实背后的数学结构,因此他认为测量悖论是量子力学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一直被大多数弦论研究者所忽视。可以说,这种分歧就像托勒密和哥白尼一样,只不过这段历史还在发生。我们暂时无法借助历史的后见之明来评价,但毫无疑问,如果有下一次科学革命,必然孕育在这一矛盾之中。
回程
通过上述事件我们发现,救赎现象贯穿整个西方历史。拯救现象就是拯救艺术,艺术和科学一样,可以给人们带来新的知识。这些新知识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通过研究这些幻象,人们也可以了解现实世界。毕竟,无论幻境如何扭曲,依然能够反映出幻境的模样。如果这个表述过于晦涩,可以用唯物辩证法的表述来代替。虚构的艺术和文学作品是对原始现实的描述。即使存在一些扭曲,这种描述仍然可以反映部分现实。这就是文学批评中现实主义分析的本质。正如丽贝卡·C·汤普森(Rebecca C. Thompson)在她的书的后记中所说:“一个故事,尤其是奇幻故事,最好能让你相信一个虚构的世界,而不需要你经历太多的心理障碍。”你想与世界和其中的人物建立联系。如果你被要求忽略太多的物理定律,或者相信太多有问题的生物学,你就会失去这种联系。现实的规则可以延伸到幻想世界。但它们需要在内部保持一致,如果不一致,即使是最细心的观众也将被迫暂停……”
正是出于拯救现象的动力,科学家们毫不犹豫地通过这些作品引入科学。不管他们的哲学概念如何,他们所做的就是找到与大家共同的想法。这样的例子在《冰、火与物理:媒介的科学》中比比皆是:是绞杀者马钱子碱,是野火希腊火,是瓦雷利亚钢大马士革钢……不完全匹配也没有为了尽可能解释其中的关系尽可能地,作者会为乔治·马丁寻找各种原因,并给出各种可能的答案。虽然这基本上不可能是马丁创作的初衷,但毫无疑问,它确实加深了我们对现实科学的理解。理解。所以当作者发现科学无法解释的时候,她也会承认这是上帝之手。毕竟,这是小说,而不是科学。她并不坚持小说一定要按照科学规律来写,她只是认为小说有自己的逻辑,但这对她来说很有趣。这不正是著名科学家面对科学研究的常态吗?
余英时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运用了库恩的理论,称之为红色学的一场革命,将红色学研究从考证探索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其内涵也是拯救现象。事实上,随着科技的发展,正如翟振明在《存在与虚无之间:虚拟现实中的哲学历险》中所讨论的那样,虚拟现实很可能会变得与现实难以区分。另一个众所周知的说法是:我们的现实世界是模拟的吗?这似乎又回到了埃舍尔的画作(见下图)。是我们模仿他们,还是他们模仿我们?近年来,一些影视作品讨论了此类话题,例如韩剧《W-两个世界》。虽然今天我们面对维斯特洛和大观园,知道它们是虚拟的,认为讨论这类作品的实用价值是个脑子问题,但实际上我们从古希腊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问题,并且不自觉地用它们来理解其他世界。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个人类历史上观察异世界的真实案例。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除了四种元素之外,还有第五种元素——以太,它就在月球和月上带之上。天使或神灵所在的地方,一切都是完美的,但只有下月区才有四种元素。两个世界的运行规则完全不同。然而,一个名叫伽利略的人突然灵机一动,把他新发明的望远镜对准了月球,却发现月球上布满了凹坑和瑕疵。每个人都知道其背后的故事。
西方自然哲学家(科学家)太习惯这种思维和叙述方式了。人类在拯救现象的同时,也在思考自己和宇宙,这条路还远未结束。
后记
大量这样的作品,从国外的超级英雄物理学到国内的三体物理学,都是这样做的:他们用现实生活中的物理学来保存和解释书中的现象。真假并不重要。这自然是有缺点的。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阻碍想象力,即强迫大家接受科学概念来解释超级英雄等作品,文本的多样性就会大大降低。在我对漫画的一些分析中,微博电影和《三体》的评论中多次提到了这一点。

此外,有必要对近年来中国科幻界重新发明的科幻现实主义进行梳理。这种说法认为,科幻小说的目的可以是反映现实,科幻小说的方法可以是现实主义的。其积极意义在于指出科幻小说的目的也应该是人类,正如科学的目的不是科学而是人类一样。看来它把科幻小说从科学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但是,如果结合我们之前的分析,我们会发现这种说法并不是很站得住脚。这是原因之一。所有的作品都描述现实,哪怕是幻想或夸张的现实。 (在真正的虚拟现实到来之前)本质上,任何文学和历史都是对现实物质世界的描述。任何作品都是现实的体现,正如郑文光早在1981年就指出的那样,“科幻小说也是小说,也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但它不是像平面镜那样的反射,但折射镜……采取严肃的形式,我们称之为科幻现实主义。”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原因,科幻现实主义是重新发明轮子,但根本没有解决问题,郑文光因此指出,他希望创造“社会科幻”这样一种探讨社会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小说。 “把它视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部分”,这是为了区别于过去那些理想化、宏大的科学。这样的划分很难不让人想起另一个非常现代的范畴。体裁文学——悬疑小说的分类方法,正如悬疑小说的划分一样很快,中国科幻小说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将郑文光的提法发扬光大,但这个名字变得更加流行:硬科幻和软科幻。
软科幻和硬科幻的二分法似乎是基于小说中的科学“成分”,就像推理小说中逻辑推理的“成分”区分了字面推理和社会推理一样。如果今天提出的科学实在论又回到了过去的二分法,那只是老把戏换药而已。第三,抛开第一点本体论的讨论,这种区别本质上是随着人们对科学的认识而改变的。正如经济理论也讨论过科学应该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一样,文学中的科学元素是否应该被视为文本中的特例,本质上取决于科学是否与现实中的日常生活相分离?如果有一天人类社会进入全面的科学时代,科学本身内生于现实生活,那么科幻小说和今天的现实主义小说就没有什么区别了,科幻小说几乎可以对应现在的超现实主义小说。然而,今天我们需要大力宣传科幻的概念,这说明科学还没有内生于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所推崇的科幻现实主义已经成为了谎言。这种希望是荒谬的,因为它只能通过现实来实现。主义,而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由科幻小说带来。在这个层面上,试图通过科幻小说(或其他文学)来拯救现象只能引起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兴趣。这些热情和欢乐与现实世界并不相符。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并回归现实本身,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理解和改造现实世界。我们只能沉迷于幻想,以为自己拯救了现实,就像我们看山洞上的影子舞动一样,或者只是把地球放在宇宙的中心作为数学模型的平均值。
参考
[1]孙亚杰,陈志国。 “拯救现象方法”:康德先验哲学实践活动中的又一方法论因素[J].求是学术杂志, 2020, 47(02): 47-57.
[2]吴玉梅,孙晓春。霍金与彭罗斯“量子引力论”之争[J].科学文化评论, 2020, 17(01): 29-40.
[3]于继元,N.布宁.拯救现象:亚里士多德的比较哲学方法[J].世界哲学,2017(06):5-17。
[4] 熊海洋.从“拯救现象”到“拯救艺术”——古希腊艺术理论的线索[J].中外文论,2017(01):181-191。
[5]孙云龙.从救赎现象到人类解放——论辩证法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1, 40(05): 53-56.
[6]王海钦. “哥白尼革命”的另一种解读——数理哲学的视角[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09):18-22。
[7]姜振宇.贡献与误区:郑文光与“科幻现实主义”[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2017(08):78-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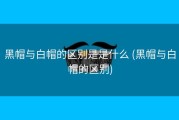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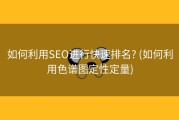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