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上海的双重性格:小资天堂与小市民世界的完美融合

上海是小资的一个天堂,同时也是小市民的一个世界,这里充满了烟火的气息以及市侩的味道。每一个真正的上海人,都拥有着两张脸:一面是浪漫的小资,另一面是功利的小市民。如果缺少了其中一面,那就都不是典型的上海人。
许纪霖为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同时也是历史系博士生导师。他主要致力于 20 世纪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的研究工作,还进行上海城市文化研究。他著有《脉动中国:许纪霖的 50 堂传统文化课》《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等作品。
文/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
01.
上海被称作魔都,她具有阴性特质,魔性尽显,宛如《繁花》里那种变化多端的上海女性。
上海呈现阳性特征,它兼具柔和与刚强。在血脉传承中,继承了“江南侠客”鲁迅的基因。每当处于历史的紧要关头,它都会挺身而出,去扭转命运的齿轮。
一个国际大都市,既有阴又有阳,刚柔相互结合。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揭开她那神秘的面纱呢?又怎样从历史的轨迹以及现实的情况中,去窥见她的真实面貌呢?
从电视剧《繁花》开始说起吧。繁花的热度使得这个冬天的魔都有了些许温度。黄河路、进贤路以及和平饭店处打卡的民众接连不断。这是在向不朽的传世小说作者金宇澄表达敬意,也是在向成功改编为电视剧的王家卫表达敬意,同时还是在向这座魔幻的城市表达敬意。
读过小说《繁花》的文青,如果仔细研读,就不会认同王氏连续剧。因为王家卫只是抽取了小说中的一些零星话语,然后演绎出了繁花中的一条脉络、一个时间和一个空间。记忆必然伴随着遗忘,小说中有那么多精彩绝伦的片段都被删减掉了,这让文青们怎能不感到心痛呢?他们会有一种被玩弄的感觉。
新上海精英们毕业于 985 名校,然而他们也看不懂电视剧《繁花》。她们对于魔都的想象,源自于王安忆的《长恨歌》、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以及邵艺辉的《爱情神话》。这些作品所呈现的世界充满了传奇、高雅与罗曼蒂克,仿佛是一个空气中都弥漫着玫瑰花香的楚门的世界。
王家卫让她们感到失望。她们看到的是黄河路上那激烈的商战,进贤路中那些小市民的相互争斗,以及上海小女人的那种咋咋呼呼。
这是魔都吗?这是梦幻中的东方巴黎吗?
然而,老上海人认可王家卫。游本昌、马伊琍、陈龙等这些说着满口俚语的人,让老上海人从他们的乡音中找到了熟悉的烟火气。魔都并非只有霓虹灯和梧桐树,还有那些在霓虹灯光亮照耀不到的地方,比如亭子间、七十二家房客,会为一毛三分钱水费分摊不均而打官司,吵得昏天黑地。
王家卫拍出了另一个上海,这个上海处于野蛮生长的时期,是一个小市民的世界。
这样的野蛮生长,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清末民初,第二次是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也就是魔都的二次开埠时期。
三十年代的海上有着旧梦,今日的魔都呈现出婀娜多姿的模样。它们的前世今生,都源自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蕴含的狼性。文明的源头,就是野蛮。
上海是小资的天堂,也是小市民的世界,充满了烟火气和市侩味。每一个地道的上海人,都有两张脸:浪漫的小资和功利的小市民。缺了一面,都不是典型的上海人。
小资具有雅的特质,小市民具有俗的特质。然而,魔都的文化处于雅与俗之间:既追求雅,又展现俗;能够将俗转化为雅,做到雅俗都可以欣赏。
老上海人在《繁花》的字里行间能认出自己,在飘忽的镜头夹缝中也能认出自己。
《繁花》热度呈现冰火两重天的态势。它在老上海人中热烈燃烧,却不为新上海人所理解,还遭到全国观众的冷落,这并不奇怪。原因在于新上海人未曾经历过那个野蛮生长的岁月。而对于老上海人来说,在《繁花》中看到的,既是记忆里的城市成长史,也是他们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
在外滩、新天地以及陆家嘴打卡的外地游客,还有居住在联洋社区、仁恒滨江以及古北新区的沪上新贵,他们对《繁花》的小市民世界都很生疏。新的社区中彼此独立且陌生的生活,消解了石库门里弄中那种相爱相仇的邻里关系,而这正是《繁花》中葛老师的租客们的真实相处状态。同时,王家卫残酷地唤醒了老上海人的童年记忆,这种记忆既亲切又残酷。
上海在不同空间呈现不同面貌,魔都在不同时间也有所不同。倘若说王家卫存在什么不足,那就是他的空间感是正确的,而时间感存在错误。王导对上海的空间元素有着极为高超且直接的把握,但对于九十年代的上海,他毕竟还是比较生疏和隔膜的。剧本是由上海女生秦雯编写的,然而当还原到屏幕上时,墨镜王只能依靠《上海滩》那样的港味民国来想象魔都的第二次开埠。
他很聪明,设计出了一个小说中原本没有的爷叔。这个爷叔,在民国时期从事跑交易所的生意,是上海商业精神的具体体现。他常去和平饭店,是这座城市的主人。曾沉寂了半个世纪,借着上海二次开埠的契机,又重新回到了远东第一大饭店。
爷叔这个形象在《繁花》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这使得电视剧有了灵魂。他把民国和 90 年代的上海连接在了一起,跨越了中间的歧出阶段。如果没有爷叔,就不会有黄河路的宝总;而如果没有宝总,从精神层面上来说,爷叔也是死亡的。这两位上海商业精神的代表,将新旧上海全面贯通,就有了一部能够穿越时代的直通车。
难怪网络上出现了一张图片,那是爷叔的背影:在 2024 年,希望你能拥有一个像爷叔一样的人。
爷叔乃是上海历史的具象体现。一座城市,倘若具备优良的基因以及良好的历史,在城市竞赛的起始阶段,无需率先起跑,就已然等同于赢得了半个优势。
论改革开放的时间,深圳比上海早一年。它的前身如同一张空白的纸,虽可描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但在空间上缺乏曲折迂回,在时间上少了些纵深之感,没有过往的积淀,底蕴不足。
深圳有爷叔,那是隔壁的香港。不过,那位爷叔如今迷失了方向,得靠深圳自己去闯荡天下。若论闯荡,深圳始终领先于时代,在 80 年代是进行来料加工,到 21 世纪则转型为中国的硅谷、民企的中心。尽管深圳在经济上能驰骋天下,但在文化上依然显得年轻稚嫩。经济的崛起,一代人就可以做到,而要成为文化大都市,非得三代人之后不可。
与深圳相比,上海的崛起稍晚,晚了 12 年。上海看似不声不响,实则一鸣惊人。人们往往只注意到浦东陆家嘴的摩天大楼、金桥和张江的高科技。然而,魔都的最大魅力实际上仍在浦西,在于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会、梧桐区的高雅街区以及新天地的时尚地标。
那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底蕴。这种底蕴,正是爷叔所代表的近代上海。
02.
近代上海,给魔都的二度开埠以及崛起,留下了何种城市文化传统呢?
上海作为一座口岸城市,它的诞生和崛起是全球化的产物。外滩有万国建筑,梧桐区有法式别墅。影响上海的外来文化十分复杂,其中有西洋的英国文化、法国文化、俄国文化、美国文化以及犹太文化,还有东洋的日本文化。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异域文化都聚集在上海,共同塑造了近代上海的城市文化传统。
上海的城市文化型塑,其中公共租界所代表的新教文化以及法租界所代表的拉丁文化,是两个最为核心的外来元素。
新教传统在上海城市精神里最为显著。中国人中,上海人对待工作极为敬业且十分拼命。上海的城市节奏比其他城市快很多,许多新移民来到上海,最初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饮食不习惯,而是生活节奏和心理节奏太快,难以跟上,甚至走路节奏也跟不上。
上海人擅长算计,在各个方面都展现出了细微之处的精明。这种精明,正是马克思·韦伯所提及的工具理性。朱镕基当年在上海担任市长时,曾批评上海人虽然精明但不够高明,在小的地方算计得很精细,然而在大的价值目标方面,未必能够达到高明的程度。
国人当中,上海人比较有职业感且讲信用。新教传统在上海和香港都存在,然而对比上海,香港仅有一种新教精神,却缺少另一种文化的平衡,而这种文化平衡就是上海所拥有的天主教拉丁文化。拉丁文化的浪漫、超脱、伤感、颓废与基督新教的理性、世俗存在很大反差。上海人具有小资情调,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此。
上海人的血脉中,既有紧张的特质,也有潇洒的特质;既有世俗的一面,又有超脱的一面。一张一弛之间,颇具平衡感和对冲感。
近代上海具有文化传统,洋风虽盛但仍有本土传统,此本土传统为明清以来以江浙为代表的江南文化。江南文化有两个特点,其一为清代考据学派所体现的理性传统,其二是以苏州评弹、绍兴越剧为主流的才子佳人传统。
江南文化的这两种传统,在近代以后与外来的西洋文化形成了奇妙的对应。考据学派的理性传统与基督新教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上海人特有的理性、世俗和实干精神;才子佳人的浪漫温情与天主教拉丁文化产生化学反应,使得上海人在生活方面比较细腻精致,懂得如何生活,懂得享受艺术,能够将日常生活审美化。
《繁花》里,魔都文化的张力在阿宝、玲子、汪小姐身上展现得极为充分。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城市的基因一直顽强地代代相传,只有上海是魔都,只有上海人才具备魔幻、古怪的性格。
03.
进一步追问的话,上海的城市文化性格,究竟是什么?
作为城市游走者且研究过此问题,我的回答简单,十二字:海纳百川与时俱进务实浪漫
先说海纳百川。
上海文化包容多样,能接纳各方之风,兼具中西特色,南北皆通。它是一种似洋泾浜般的文化,既非纯粹的中,也非纯粹的西,而是亦中亦西。若用一个字来概括上海文化,那便是“海”。海极为辽阔且博大,能够容纳众多河流。众多河流汇入大海之后,便不再是单独的河流,而是汇聚成了一片文化的大海。无论是白昼还是夜晚,都呈现出千变万化的景象,美丽绝伦,魅力无穷。
上海如同纽约,是一个移民的大熔炉,也是一个文化的大熔炉。所有的地域文化、宗教传统和高级文明,来到上海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最终都逐渐失去了其原本的模样,演变成了极具都市风格或东方神韵的“海派”。海派西餐、海派西装、海派英文(洋泾浜英文)、海派川菜、海派京戏,这些都是外来文化被融合、被改造的典型例子。
上海是一个口岸都市,它的吞吐能力很强,胃口极好,能够吸纳各种相互矛盾、对立冲突的文化,实行拿来主义,对来者一概不拒。同时,它又有同样强大的消化能力,既能化腐朽为神奇,也能化神奇为腐朽,能够将各种不相关的元素进行混搭,从而做出一道有风味的海派大餐。
上海是一个大的展示码头,也是一个文化的搅拌机。它见多识广,眼光挑剔,同时又宽容并蓄,能够点石成金。上海文化的优势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开放,二是杂交。开放与杂交相结合,就会产生创新。
北京能够容纳不同的事物。各种多元文化以及区域文化都可以在京城以原本的状态独立地存在,它们之间互不影响,同时还会彼此展开竞争。上海文化的凝聚力十分强大,各种亚文化来到上海之后,都被这座魔都进行了改造并使之同化。
上海文化的一个缺点在于缺乏特点,没有那种独一无二的事物。所见所闻皆似曾相识,同时又带有一丝陌生之感。然而,恰恰是这种没有特点的状态,恰恰成为了上海文化的最大特点。
再说与时俱进。
上海有两次开埠,这两次开埠都是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以及在向国际开放的过程中去谋求生存和谋求发展。上海能够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它抓住了当时的时势。上海人对时势有着最为深刻的理解,懂得识时务者为英雄的道理。
时势总是不断更新。外部的空间和时间发生了变化,那么时势也会跟着发生改变。上海处在国际化的前沿位置,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就是顺应时势,持续地追求变化、追求创新,并且做到与时俱进。
上海人不太恋旧,也不局限于传统,对新事物和新观念总是怀有跃跃欲试的兴致,乐于走在时代前沿,喜欢掌控潮流、引领时尚。在明清时期的江南文化里,就已显现出这种迹象。到了晚清民国时期,其摩登时尚,不但在神州独领风骚,而且在东亚也处于领先地位,在世界上也颇为得意。即使是在充满清教徒精神的革命年代,上海依然保持着时尚的本质。它擅长在整齐划一的氛围中去把握个性。当年,上海产品在封闭的环境下能够畅销全国,靠的就是这些独特的方式。
第二次开埠之后,与时俱进的精神传统愈发明显。所有的文化、观念、建筑以及商品,都需要与全球最先进、最时髦的水准相契合。它既造就了上海的摩登、时尚与辉煌,同时也使得上海文化具有流质易变的特点,缺乏底蕴;显得灵活有余,但定力不足。它有见世面、识大体的小聪明,却缺乏北方古城那种自信、稳重的大气象。
最后是务实浪漫。
海派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扎下了根。海派文化具有世俗的一面,同时也很务实。上海人不像英国人那样喜欢高谈阔论,也不喜好抽象的理念教条。他们源于生活,更信赖经验,相信由日常生活升华出来的常识理性。
上海人做事多于言语。他们信奉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而非在话语上争得先机。上海人很实在且靠得住,不会轻易许诺,可一旦许下承诺,就会认真地去实现。
上海拥有国内较为少见的职业精神,把平凡的职业当作志业,能在繁杂的俗务里创造出美感,营造出情调,展现出诗意。在这方面,上海人就如同法国人一样,不单单满足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本身,始终在追寻世俗背后所蕴含的浪漫,以及实用背后所具备的格调。
上海人的身上有着明清士大夫的精神血脉。他们的日常生活或许并不奢华,然而一定是精致的。他们的情感或许并非真诚,不过一定是浪漫的。上海人重视形象,注重包装,对外在的那层气质、品味和格调格外在意。
上海的务实展现出布尔乔亚精神;上海的浪漫呈现出波希米亚人的风格。然而,极端的资产阶级和流浪文人的精神,以及极端的英格兰和法兰西传统,在上海却难以行得通。上海并非一个走极端的城市,它时尚却不前卫,叛逆却不偏激。上海城市精神的中庸性格和中道哲学,将那些偏激的传统筛选掉,留存下了中间的市民文化和小资文化。
市民阶级具有务实的特点,小资文化呈现出浪漫的特质。这两种文化性格在上海并非有着绝对的界限。在最为典型的上海人身上,务实与浪漫同时存在,相互衬托,更加彰显各自的优势。上海男人的可敬以及上海女人的可爱,都源自于这种务实与浪漫兼具的特质。
04.
《繁花》所描绘的上海,和如今的魔都不同。历经 30 年的时光变迁,上海从之前的野蛮生长状态转变为如今的温文尔雅,气质独特。就像上个世纪 30 年代的魔都那样,曾经的暴发户如今变成了都市贵族。
上海曾是中国的文化中心。1949 年之后,被平调到了北京。经过 80 年的发展演变,文化中心的重要位置又倾向南方,回到了黄浦江边。许多科技、人文、创意和艺术精英从北方往南方迁移,在张江、前滩、徐汇滨江、苏州河畔安了家。
如果把北京 798 艺术区和上海龙腾路的众多美术馆进行比较,就会看出两者存在年代上的差异。北京 798 艺术区只是 20 世纪的先锋代表,而上海龙腾路的众多美术馆则代表了 21 世纪的最前沿。
海派文学和影视曾经一度沉沦,而在这十年开始苏醒。小说《繁花》横扫了各个奖项,金宇澄获得了众多奖杯。电影《爱情神话》以及连续剧《繁花》成为了上热搜的现象级作品。
走红的影视剧推动了魔都的 city walk 这一现象。传统的南京路、淮海路以及城隍庙这些地方不再受到青睐,而武康路、愚园路、黄河路和进贤路则成为新潮青年新的网红打卡地。
不过,这些只是魔都魅力的一小部分。上海在这几年里能够引起全国以及全球的关注,是有其他原因的。
那就是2022、2023年的上海。
2022 年春天的魔都,即便处于极为极端的状况之中,身处困境的上海人依然保持着生活的镇定以及优雅。而在年底的冬天,那一把火与春天处于同一条因果的链条之上。倘若没有春天的寒冷凛冽,就不会有冬天的熊熊燃烧。
魔都时常被各种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进行过多的政治方面的解读,这会让真正了解上海的人觉得十分可笑。
魔都与帝都不同。帝都从各个方面都布满了政治细胞。而魔都具有文艺和社会的特质。这座城市呈现出阴性的存在状态。在魔都,女性比上海男性更值得被尊重。
2022 年的春天,全国人民最为惊讶的是静默期间的一个场景。一位男士在小区理发,而交响乐团的小姐姐正在演奏小提琴为他增添乐趣。这个场景既显得荒谬,又显得高雅。正是因为其高雅,才显得荒谬;也正是因为其荒谬,才更显高雅。
2023 年的上海万圣节和平安之夜可以这样解读。这种文化狂欢是群体性的,在中国只有在魔都才会出现,且没有其他地方能与之相比。
巨鹿路上,各种事物都能进行 COS ,这隐喻着上海年轻一代的酒神精神;而静安嘉里中心那棵高达 20 米的圣诞树屋,它是魔都坚守全球精神的一种不屈的象征。
上海为何重新获得了全国的关注呢?我经过观察发现有两个秘密,其一在于职场人士,其二在于年轻一代。
上海集中了数量最多的中国商务高楼,同时也汇聚了全国数量最多的职场人士。这些白领以及中产阶层,他们是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是国家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并且也是社会文明的关键支柱。
20 世纪末时,改革的核心动力源自大学,其中包括致力于启蒙的教授学者以及血气方刚的大学生。到了 21 世纪,这种动力逐步从校园转移到了社会,并且从知识分子转变为了职场人士。
北京在知识分子方面领先于上海,而上海在职场人士方面胜于北京,这便是这几年京沪风水发生变化的底层逻辑。
中产阶级并非仅为财产概念,而是一种结构性存在,这正是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各个城市中,没有哪一个城市比上海拥有更深厚的市民社会传统。其历史渊源始于工部局的侨民自治,这种自治逐渐弥散至全市,从而造就了上海市民的权利意识和自治传统。在上个世纪的 20 年代和 30 年代,上海的市民社会与城市自治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
2022 年的春天,上海处于静默状态。上海市民自发地进行自救。许多职场精英站了出来,担当起团购食物的团长这一角色。他们接管了瘫痪的社区日常管理事务,积极应对各种紧急状态。这些行为无疑是对民国自治传统的继承。
市民与公民有所不同,市民没有那么高端大气、充满激情。市民较为平庸,他们只在意日常生活里的柴米油盐等琐事;然而市民又很了不起,他们不在乎那些抽象的正义观念,却会为了自己的生存权利而奋力拼搏。市民当中的精英,也会具备公共精神,就如同传统社会的乡绅一样,为百姓申述请求,提供公共物品。
90 年代初处于《繁花》时期的时候,宝总、陶陶、玲子以及汪小姐等人刚刚开始崭露头角。那时只有市民存在,而还没有形成市民社会。经过了三十年的不断积累,上海的市民社会逐渐聚集起来,如同沙粒堆积成高塔一般,在默默之中生成了。
你身处魔都,会有如下感受:高天之上,寒流急速涌动;大地之上,微微有暖气吹拂。体制之内和体制之外,仿佛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有着两个不同的季节,也有着两种不同的温度。
市民社会具有中庸且保守的特点,中产阶级属于稳重的秩序群体。然而在当代魔都,除了职场人士所秉持的布尔乔亚传统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属于年轻一代的波西米亚精神。
去年魔都的万圣节狂欢,年轻人进行集体 COS,其美令人震撼全国,也惊动了全球。从 2022 年到 2023 年,一种以上海为中心的新人类文化,正在中国逐渐显现。
老一代人如同九斤老太那样,时常抱怨当下的年轻一代过于消极、懈怠、不作为,对他们恨铁不成钢。然而,新一代人的突然出现,以独特的方式挺身而出,让父辈一代大为惊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儿女们。
他们是熟悉的,每当历史处于关键时刻,总会有年轻人热血沸腾;而那些老于世故的中年人,仅仅是在一旁旁观的看客;年轻一代又显得陌生,他们的那种姿态、那种风格太过新潮,从未曾见识过。
不错,千禧一代(1985 - 1995 年出生)是当代中国的新人类,Z 世代(1995 - 2009 年出生)也是当代中国的新人类。新人类必然有新文化。这一新文化在虚拟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万圣节也展现得清清楚楚。
年轻一代是不在场的。他们拥有自己的人生避风港,其中包括手游、VR、剧本杀、动漫二次元等。这些是老一代人所陌生的虚拟世界。
90 后和 00 后在现场。疫情过后,各类大型演唱会、跨年庆典、CP 动漫展非常火爆,门票很难买到。宅男和宅女们纷纷出现,展现自己的个性。年轻一代存在矛盾,他们越是习惯于独自面对电脑,在虚拟世界中展现自我,就越渴望在现实世界的集体空间里,以匿名的方式参与狂欢,暂时放下“自己”,全身心地融入到癫狂的“集体”中。
万圣节的 cosplay 是连接两个世界的最佳途径:在现实空间里演绎二次元;用活报剧来针砭当下的内卷;以喜剧的形式悼念记忆中的悲苦。
万圣节盛况是自发形成的,不要认为这是偶然的突发奇想,因为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每年有两届的 CP 大会,这就像是平时的操练,到现在已经持续了 28 个年头。从第一届时只有不到 20 个摊位,100 个人参与,到去年五一节的第 29 届,已经有 30 万人次了,各路 COS 大军在最顶尖的国家会展中心竞相展现美丽。全国的目光聚焦在淄博烧烤之时,一二线都市年轻人却未给予这一盛会应有的重视,忽略了其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
青年文化方面,上海扮演了重要角色;cosplay 领域,上海也担当了龙头的角色。原本属于北京的波西米亚精神,因沪漂的汇聚,在上海也得以弥漫。布尔乔亚文化与波西米亚精神在上海并非完全割裂:一个上海的白领,白天是受 KPI 约束的布尔乔亚,晚上则可能成为大胆叛逆的波西米亚人。肉身是顺从的,灵魂是反叛的,它们组合成了在应试教育中早就练就的那种双重人格。
更重要的是,魔都现今拥有能支撑青年文化的一整套新媒介机制,其中包括澎湃、B站以及小红书。上海并不具备腾讯、美团、百度、字节跳动和阿里巴巴这样的大型互联网商业帝国,仅有一个从外地引入的拼多多。上海人的特质并非狂野,而是以专业的态度,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件事情中,从而在细分领域成为行业的领军者。
在世纪之交都市报引领风骚之时,上海的媒体在与广州南方系的竞争中处于下风,更难以与京城相抗衡。到了网络媒体时代,上海实现了弯道超车,澎湃、界面新闻、上观新闻这些媒体虽然属于官方媒体,但它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没有官腔,为新人类文化在魔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新一代文化的直接塑造者是 B 站和小红书。如今,B 站所在的五角场已成为魔都青年文化的中心,并且带动了一批创意企业入驻。当你在五角场地铁下车时,迎面而来的是充满荷尔蒙和多巴胺的青春气息。
日前我受邀参与今年的 B 站百大 UP 主颁奖盛典。在得奖者当中,有来自美国的小姐姐,有负责猫与老鼠动画制作的人员,有从事殡仪馆化妆工作的人员,还有乡村小兽医。这些都是各种边缘领域的人物,然而他们个个都是拥有几百万粉丝的 UP 主。B站尽管在经营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却创造出了一个只属于年轻一代的平行世界,这个世界具有非常浓厚的都市气息和青年特质。
小红书主要专注于时尚、旅游和美食领域,它更是都市雅皮士的理想之地。其受众大多为都市女性,与魔都的气质十分契合,呈现出阴性、雅致且摩登的特点。登录小红书,就如同在上海进行 city walk 一样,即便身处其他地方,也能拥有上海人的精神。
05.
从《繁花》到万圣节,这就是上海的前世今生。
假如没有前世的那些“繁花”,那么就不会有魔都现在的“万圣”;如果不再有去年的“万圣”,曾经的那些“繁花”又能有什么价值呢。
春夏秋冬,历经不同的季节时光。黄浦江在流淌,苏州河也在流淌。一眼望去,看到的还是那条江、那条河;仔细端详,却发现已不再是原来的那条江、那条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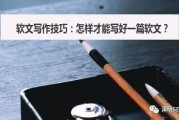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