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萌化到反政治萌化:当代青年政治主体性的动态演变与成年文化崛起
摘要:“政治萌化”是当代青年在新媒体时代进行政治参与的一种公开表达形式。自其兴起后,“政治萌化”逐渐获得了主流媒体的认可。有趣的是,在 2020 年初,身为发起人的青年主动扛起了“反政治萌化”的旗帜。青年的政治参与从“政治萌化”到“反政治萌化”,经历了身体在场这一阶段,也经历了沉浸式狂欢,还经历了理性化批判的流变。这反映出当代青年政治主体性在建构、再构与重构方面的动态变化,同时揭示了以“萌”为核心的儿童文化在消减,具有青年特征的成年文化在崛起。
关键词:政治萌化;反政治萌化;青年;政治主体性
“萌”源自日本的动漫文化。起初,御宅族们用它来表达对动漫美少女角色的喜爱,并且因喜爱而进入一种热血状态。之后,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系列的动漫“萌”产物。“萌”在中文里原本指植物发芽,后来引申为事物最初发生的状态,蕴含着新生与生机的意味。日本的“萌”文化传入中国后,它的二次元色彩与汉语含义发生了“化学反应”。在嫁接、变异与本土化的过程中,“萌”演变成了去成人化、可爱且具有减压作用的文化。青年借助互联网这一强大的力量,使“萌”文化持续发酵。“萌”逐渐成为当代青年的日常审美,并且参与到政治、经济、文化的生产中,衍生出了很多创意文化,其中“政治萌化”就是其代表。代青年发起了“政治萌化”,“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等主流媒体逐步对其表示首肯。2020 年初很是饶有趣味,发起人的当代青年在那时主动扛起了“反政治萌化”的大旗,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本文以“政治萌化”到“反政治萌化”的发展流变过程作为基础,对当代青年政治主体性的建构、再构与重构的动态发展变化进行分析,揭示出当代青年的政治参与从低幼化的身体在场转变为成熟化的理性批判。
一、“政治萌化”的兴起:青年政治参与的身体在场

21 世纪包含网络时代和新媒体时代,新媒体的出现使得符号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改变。当代青年是网络原住民,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必然深受其影响。在此期间,当代青年顺应形势,积极参与到新媒体文化的创作当中,引领了众多时代潮流,其中“政治萌化”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当代青年将往日政治所给人的严肃印象进行了改变,他们通过流行于网络的“萌化”方式来参与政治,并且借此抒发爱国情怀。
1.“政治萌化”的内涵
有网友把“政治萌化”和“政治娱乐化”视为等同。这两者都是新媒体泛娱乐化思潮的产物,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把握“政治萌化”与“政治娱乐化”的差异,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政治萌化”的内涵。“政治萌化”与“政治娱乐化”相比,有两个典型特征。其一,“政治萌化”有特定的对象,那就是青年群体;其二,“政治萌化”有特定的语言符号体系,也就是“萌”元素的加入。
但“政治萌化”作为植根于新媒体的新兴网络用语,学术界并未对其内涵形成统一的诠释。综合分析当代青年所创造的各种“政治萌化”现象,能够理解为当代青年以新媒体作为平台,运用拟人、拟物的修辞手法,通过增加“萌”元素的创作方式,对具有政治色彩的现象进行符号化解读,以此来表达某种政治情感,尤其是抒发爱国情怀的活动。“政治萌化”因为时间热度具有持续性,并且能表达爱国情怀,所以得到了主流媒体的喜爱。接着它发展到了“官方发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政治萌化”已经成为主流媒体主动发起的一种手段,是以主流媒体为平台,以当代青年为宣传对象,通过增加“萌”元素的方式来增强主流正能量宣传效果的。由此可见,“政治萌化”的内涵处于动态发展之中:起初是由青年发起,后来变为主要由主流媒体代表发起;原本是作为政治情感的表达工具,之后变成了官方的正能量宣传手段;然而,其本质始终都是二次元“萌”文化与政治情感融合发展所产生的结果。
2.“政治萌化”的初显:青年“萌”文化的符号创造
十年前,网络范围内政治与动漫的界限十分分明。热衷于政治的青年和喜爱动漫的青年彼此“看不惯”。然而在 2010 年左右,一部名为《黑塔利亚》的日本动漫打破了这一界限。这部动漫以世界历史为主要线索,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拟化成动漫人物,展现出了各国的风土民情。《黑塔利亚》传入中国后,热衷政治的青年从其中得到启发,喜爱动漫的青年也从中获得启发。他们在政治与动漫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以此来抒发爱国情怀,而这一“桥梁”就是“政治萌化”。自此,青年开始走上“政治萌化”的探索之路。
青年在“政治萌化”兴起阶段的政治参与呈现出感官先入和身体在场的特点。他们通过创作、使用和宣传各种“萌化”符号来满足感官刺激,从而进行政治参与。其一,青年借助对政治人物进行视觉图像化加工这一方式,创造出虚拟偶像、表情包等“萌化”符号,以此传递出政治参与的信号。新媒体时代,图像成为青年交流与表达情感的重要语言符号,且取代了文字。感性直观的图像与娱乐化、消解性的青年亚文化具有一致性。政治人物是政治的“代言人”,也是网络上的“红人”,他们的言谈举止在互联网环境下能被无限放大,还可进行政治化解读。这促使青年有可能通过将政治人物进行虚拟偶像与表情包创作来参与政治,并且这种行为迅速流行起来。
2013 年,动漫视频格外引人关注。在这个视频里,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被拟化成了形象的动画卡通人物,还配有融合网络流行语的字幕。其目的是向网友科普中国主席以及美国总统当选的流程。抱歉,这个问题未找到相关结果。
其次,青年进行政治参与的方式是冠以政治象征物昵称。他们依据政治象征物的特点进行创作,以网络流行词为参考,从而创作出带有“萌”元素的昵称。例如,青年网友亲切地称呼国家领导人与夫人彭丽媛为“习大大”“彭麻麻”。
最后,青年通过给予政治事件“萌”语言评论的方式来进行政治参与。青年把“萌化”昵称和网络流行语融合在一起,进行组词再造,然后在网上发布“萌化”言论并且相互传播。例如,用“我也是醉了”“本宝宝”等话语来调侃政治事件。
3.政治参与中的爱国情怀:青年政治主体性的建构
“政治萌化”兴起时,青年先是“感官先入”,接着“身体到场”,而后“思想跟进”。同时,这也是青年政治主体性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青年通过抒发爱国情怀,逐渐从自发的状态走向自觉的状态,从而完成了政治主体性的建构。
起初,动漫在青年圈层流行起来,这使得单纯的视觉享受成为“萌”文化发展的核心要素。之后,这种“萌化”的情感表达方式激发了青年投身于“萌”文化的政治性创作,以及将爱国情怀进行“萌化”表达。抱歉,您的问题我无法识别。
古语言:家和则万事兴。国家领导人的家,一方面是“小家”,另一方面更是广义上的“大家”。青年正借助这首歌,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进行了诠释。
“萌化”符号的创作题材源自现实,青年通过对题材进行深入思考和个性解读来进行创作,凭借青年的集体智慧和情感认同而走红。“政治萌化”符号的创作与使用蕴含着青年一代浓厚的爱国情和真挚的爱国心,这种爱国情和爱国心虽然浓厚且真挚,但也尽显感性。青年深刻地表达了“我爱我的祖国”的情感,然而却缺乏“我为什么爱国”这方面的认知,缺乏“我爱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的了解,也缺乏“我要怎样爱我的国家”的内在认同感,而这些都是一种自觉的境界。
青年的思考不断深入,动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突然出现。它的迅速爆红表明青年一代在政治主体性的建构方面,从自发的状态转变为了自觉的状态。《那年那兔那些事儿》以动物漫画的形式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重大历史事件,如中美关系等。这体现出青年开始真正走进祖国的历史,他们回顾祖国的发展历程,关切祖国的未来发展,感受祖国强大的魅力,对爱国精神的阐释也更加深入。一时间,观看“兔漫”成为青年的“爱国必修课”。青年深入了解政治事件,对政治事件进行个性解读,创作“萌化”符号,融合爱国情感,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建构了政治主体性,并且从自发状态走向了自觉状态。
二、“政治萌化”的盛行:青年政治参与的沉浸式狂欢

在新媒体时代视觉化传播潮流的影响下,在抒发爱国情怀的价值引领之下,“共青团中央”“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认可了青年的“政治萌化”。接着,当代青年在新媒体的“盛宴”之中以及主流媒体的“庇佑”之下,沉浸于“政治萌化”的创作,为青年群体策划了一场沉浸式的狂欢。沉浸式狂欢奏响了危机的前奏,青年陷入了一个陷阱,这个陷阱就是政治参与低幼化。危机的出现促使青年政治主体性进行重构。
1.“政治萌化”盛行的原因
新媒体促使了“政治萌化”的出现,这是毋庸置疑的。“政治萌化”获得了成功,然而同样作为新媒体产物的“网络直播”却屡屡受到批评。“政治萌化”策略能够取得成功的秘密在哪里呢?究其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青年对儿童文化怀有留恋之情,这是推动“政治萌化”盛行的力量源泉。在传统媒体时代,政治属于高高在上的精英政治,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而到了新媒体时代,在泛娱乐化思潮与消费主义风气的影响下,政治的严肃性与权威性被解构了,从而使得政治能够以轻松、搞怪的方式呈现出来。青年对政治有了新的参与需求,这一需求伴随政治严肃性与权威性的解构进程而出现,“政治萌化”成为满足这一需求的工具。“萌”文化具有去成人化、可爱和减压的特点,所以“萌”是未成年文化乃至儿童文化的表现。“政治萌化”虽由青年发起,但并非青年文化,其盛行体现了青年对低幼儿童文化的眷恋。当代青年大多为独生子女,是在几代人宠爱中长大的。青年已不再是儿童,然而在某些方面,父母仍将青年当作儿童对待,以低幼化方式照顾青年,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干涉青年的选择,以此维持自己作为父母的权威优势,实则是对青年本应具备的独立性与叛逆性造成了致命打击。在网络时代消费主义风气盛行之时,为诱惑青年冲动消费,到处都有充满“童趣”的幼稚广告。这些广告使得青年始终难以割舍对早已不属于他们的儿童文化的留恋。面对学业和生活中的种种压力,青年选择了低幼儿童文化来逃避现实,试图回到无忧无虑的儿童时代。青年通过沉浸式的“萌化”政治参与,获得了情感上的共鸣,他们快乐得如同一群未长大的孩子。
第二,官方对“政治萌化”的认可起到了推动“政治萌化”盛行的作用。主流媒体肩负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任务,然而其官方化、严肃化的传播语言难以吸引青年群体的目光,导致发展遭遇瓶颈期。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萌化”无疑为主流媒体突破瓶颈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发展策略。此外,“政治萌化”所传达的爱国情怀与主流意识形态是一致的。青年借助“政治萌化”来表达他们这一代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抒发他们这一代见证祖国繁荣强大的自豪之情,凝聚他们这一代对国家风调雨顺、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而这些都体现着主流媒体传播的主流意识形态。每一代都有独特表达方式且区别于其他时代。“政治萌化”是当代青年爱国情怀的一种时代性表达,这种表达是在遵循主流意识形态规约的前提下进行的。基于此情况,主流媒体对“政治萌化”给予了制度化认可,并且走上了主动发起“政治萌化”的道路。然而,主流媒体却没有意识到这种策略可能会导致权威缺失的情况。
2.政治参与的沉浸式狂欢:青年政治主体性的重构
在印刷时代,人们凭借语言的沉浸式阅读提升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新媒体时代,直观视觉化图像所带来的感官刺激让青年的思考方式发生了转变,并且他们独立思考的表达方式也呈现出了变化。2016 年,台岛女艺人周子瑜公开发表了不当言论。这一事件成为了导火索。中国青年组织了一场爱国保卫战。这场保卫战以社交媒体“Facebook”和“帝吧”为战场。他们以“表情包”为武器。这场保卫战席卷了两岸。这就是“帝吧出征 Facebook”事件。“小粉红”群体在此时横空出世。三年后,在香港乱局期间,中国青年以“饭圈文化”当作教材,以“爱国”作为主题,借助社交媒体这个平台,给港独分子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理论课。之后,“阿中哥哥”这一形象成为符号化的存在并轰动了全网,“守护全世界最好的阿中”等带有“萌化”意味的表达纷纷登上微博热搜,热度一直持续且没有减少,并且还得到了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转发宣传。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之中,青年有这样的表现:他们盲目冲动,而非深思熟虑;他们追求瞬时快感,而非规划未来;他们沉浸在行使自由表达的权利之中,而非承担理性爱国的责任。青年以“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的方式,策划了这场以粉丝民族主义为主调的沉浸式狂欢[3]。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指出:符号环境的变化如同自然环境的变化,起初都是缓慢地累积,接着便突然抵达了物理学家所说的那个临界点。这场沉浸式狂欢表明“政治萌化”已达到了其发展进程中的临界点。在狂欢的氛围下,青年能够享受到视觉上的愉悦,参与到身体的活动中,宣泄出情感,从而沉浸其中。青年作为普遍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代人,他们的视野并不狭隘。他们很快察觉到了危机的存在。当代青年明白“政治萌化”具有娱乐性且喧宾夺主,政治严肃性被解构的这种社会现状。他们也意识到在传播过程中,身体在场的“政治萌化”已经发生了“变异”。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并非“爱豆与粉丝”的关系。“政治萌化”使国家机器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被消解,青年的公民身份渐渐缩小。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当代青年主动对其政治主体性进行重构。在狂欢的氛围里,很多青年发出了一种声音,即反对身体在场但理性缺席的“政治萌化”,对把国家当作偶像的这种爱国方式提出了质疑,并且对这几场冲动的网络化集体行动进行了反思。政治主体性重构的过程是青年进行探索的过程。青年在探索时表现出迷茫。迷茫其实是对政治参与的理性思考。当代青年正在挣脱儿童世界的束缚。他们以成人的眼光来替代儿童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他们以公民的身份来代替粉丝的身份重新参与政治。他们在重构政治主体性时呼唤娱乐要适度,同时在重构政治主体性的过程中塑造出具有青年特征的成年文化。
三、“反政治萌化”:青年政治参与的理性化批判

“政治萌化”呈现出烈火烹油般的繁盛态势,与此同时,“反政治萌化”也开始露出端倪。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后,青年率先扛起了“反政治萌化”的大旗。这其中的原因较为复杂。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青年既是“政治萌化”的缔造者,也将成为其命运的掌控者。当代青年先重构了政治主体性,接着又再次构建了其政治主体性。与探索时期的迷茫状态相比,在这次“反政治萌化”运动的影响下,青年变得更加坚定且有力。
1.“反政治萌化”出现的原因
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蔓延。为收纳感染者而建造的“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其建造过程进行了直播,吸引了数千万网友在线观看。部分青年把建造机器想象成“蓝忘机”“欧尼酱”等符号形象。央视官媒在直播中还增设了助力打榜功能。对此,绝大部分青年都表达了反对的意见,甚至之前参与创作的青年也转变立场,开始站到反对的一边。青年在此公开发起了“反政治萌化”的行动,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二是……
第一,青年反对“政治萌化”这种儿童文化。如前文所说,“萌”向来不属于青年文化,它带有“儿童文化”所具有的低幼性。儿童的世界是简单且天真的,所以“政治萌化”也存在着简化现实以及扭曲现实的局限性。以新型冠状病毒被昵称为“阿冠”为例,我们能否从“阿冠”里读出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艰辛呢?能否从“阿冠”里读出生命逝去的悲痛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它所呈现出来的反而是戏谑、旁观以及无所谓的态度。“政治萌化”这种语言符号体系将政治的严肃性进行了拆解。学者指出,过于宽泛笼统的概括无法突出那些与政治以及政治关系极为密切的政治话语,并且还掩盖了其中存在的不平等的权利控制意味[5]。在日常话语中,政治意味就是这样的,而在“萌化”语言之下,政治意味还能留存几分呢?
同时,儿童文化具有低幼属性。在“政治萌化”娱乐性喧宾夺主的现状下,这一属性暴露无遗。“反政治萌化”始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阶段。那时,社会的主流情绪是严肃的,人们的无力、悲痛甚至愤怒等情感交织在一起。而“政治萌化”所具备的娱乐性与严肃的主流情绪相悖。此时,“政治萌化”的娱乐消费带有疫情的意味,这引起了青年的不适。政治是“政治萌化”的根本所在。当“萌化”成为主流时,就发出了“娱乐至死”的危险信号。在疫情当前的情况下,青年呼吁社会铭记这场“人民战争”的深刻痛楚与严肃意义。因此,青年通过“反政治萌化”来对娱乐性喧宾夺主的低幼文化进行反省与反抗。
第二,官方在对“萌化”符号收编过程中的不当反应。主流媒体主动开展“政治萌化”这一行为,是对青年“萌”的一种收编,其目的是想把“萌化”符号掌控在主流意识形态范畴之内,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却无形中展现出了权力的傲慢,这也是对青年的一种“冒犯”。“政治萌化”是由青年发起的。每一个“萌化”符号都源自青年的生活经历,凝聚着青年的智慧,还能引发青年的情感共鸣。如果官方发起的虚拟人物或形象没有根基,那么这种“主动作为”实际上是主流媒体想要以迎合青年早期的“萌”审美来夺回宣传上的话语权。这种“自上而下”的宣传方式没有以平等的位置与青年进行交流,它破坏了青年“萌化”符号的独立性,并且在客观上进一步促使青年进行独立思考。
2.政治参与中的批判思维:青年政治主体性的再构
青年政治主体性的再构是以重构为基础的。在重构过程中,青年在反思中进行尝试;而在再构过程中,青年在反思中采取行动。随着理性的回归,具有批判精神和责任担当的青年,正以饱满的状态和十足的热情投身于新时代青年文化的创作之中。
当代青年直面现实,娱乐性在其中喧宾夺主。他们面对主流媒体的“主动作为”,果断以实际行动向官方代表提出话语权诉求,此行动为“反政治萌化”。与之前的迷茫相比,青年群体如今变得更加自信且坚定。青年的政治理性与批判思维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养成,而是在社会的打磨以及舆论的刺激下,逐步形成并不断深刻化的过程。青年在批判时展现出健全且独立的人格。当面对官方代表“自上而下”的宣传方式时,他们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不再选择保持沉默,而是能够理性地表达自身的看法,并且提出与官方代表进行平等交流的诉求。可见,青年在独立思考时追求自主发展。这次的“反政治萌化”是青年群体在新冠病毒疫情的社会大环境推动下的集体公开表达,也是当代青年在疫情阶段成长成熟的表现。当代青年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这一代的责任与担当。抗“疫”期间,青年医护人员深入前线。青年志愿者站好防“疫”的每一班岗。青年党员以身作则。青年突击队成了抗“疫”的主力军。事实证明,在青年一代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作为成年人所具备的责任与担当。国家领导人曾说:“广大青年通过行动展现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非常出色,是能够担当重大责任的。”
四、结语

青年阶段是个体从儿童向成人蜕变的过渡时期,是个体发展必然要经历的阶段。青年在年龄和生理方面已经达到了成人的标准。然而,成人不只是一个年龄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7]。青年文化为成年文化奠定了主基调,青年文化是成年文化的初期表现阶段,也是成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萌化”可被视为儿童文化在新媒体中的一种投射。“反政治萌化”则展现出具有青年特征的成年文化的创造与生产。从“政治萌化”到“反政治萌化”,青年独立思考的表达方式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青年独立思考能力投射到政治参与上,就会体现出青年政治主体性的状态。青年在建构政治主体性的过程中逐步生产出成年文化,其属性为独立思考、理性批判、责任担当。从“政治萌化”到“反政治萌化”,这是当代青年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个体现。当年的青年在祖国的精心培育下已经长大。他们变得更加独立,他们变得更加自信,他们变得更有担当。但青年的爱国情始终未变,这既是青年政治主体性建构、再构与重构的精神实质,也是推动青年政治主体性积极健康发展的核心力量。
本文是 2018 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青班专项课题“青少年自创文化符号的道德引导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该课题获得了基金项目的支持。
马川: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孙妞: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龙柏林和刘伟兵对青年群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表情包路径进行了探析,该成果发表于《青海社会科学》2017 年第 4 期,其页码为 129 。
蒋磊指出萌是微时代的审美经验。该研究发表于《文化研究》2014 年第 20 期,页码为 44 至 45 页。
刘海龙指出,要像爱护爱豆那样去爱国,这便是新媒体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在 2017 年第 4 期的《现代传播》杂志中,对此有相关阐述,其页码为 27 。
波兹曼的《娱乐至死》这本书,由章艳进行翻译,出版于桂林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时间是 2004 年,其中第 34 页有相关内容。
刘迎新论述了政治话语通俗化的修辞传播。[该论述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16 年第 9 期,其所在页码为 165。
新华社称,国家领导人指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表现得非常出色,是能够担当重大任务的。
汪振军对电视娱乐化的陷阱进行了探讨,他研读了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与《童年的消逝》,并将其成果发表在《新闻爱好者》2013 年第 9 期,该期页码为 30。

提取码:ddc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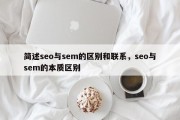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