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恨歌到儿女风云录: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变迁与人生百态
有人说王安忆是继张爱玲之后最了解上海的“海派作家”。王安忆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上海这座城市的都市生活、琐事和时代变迁。其中,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就是《长恨歌》。
《长恨歌》三十年后,王安忆出版了以男性为主角的小说《儿童编年史》。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小瑟的舞蹈家。王安忆经历了人生的坎坷,再次谱写了一部上海传记。生活和城市依然艰难、冰冷、迷人。

从《长恨歌》到《孩子们的故事》
从1976年开始文学创作到现在,作家王安忆的写作生涯已接近半个世纪。四十年来,王安忆为读者呈现了一部又一部有关上海、有关社会、有关普通人命运的作品。不过,说到他的代表作,相信很多读者首先推荐的还是《长恨歌》。 《长恨歌》详细讲述了上海女子王琪瑶与这座城市的纠葛。王德伟评论说,这部小说填补了张爱玲《传奇》、《半生》之后几十年海派小说的空白。
“老上海的面貌仿佛被时间沉积在人们的脑海里,模糊却有迹可循。轮廓就像一面古老的铜镜,每一点都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创造的,历尽沧桑。” ,但它永远不会消失。”这是豆瓣读者对《长恨歌》的评价,也是王安忆对上海的书写。如今,这段话可以用来评价王安忆的新作《孩子的故事》。
“上海一直有一种人叫老夫子,他就是其中之一。” “这座城市的年代顺序不是按时间划分的,而是按空间划分的,一个又一个的街角。”继《长恨歌》三十年后,王安忆又推出长篇小说《孩子们的故事》,以男性角色——上海的“舅舅”萧瑟为主角。小说围绕小瑟走向没落的人生展开,可以说具有颠覆性。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但他年轻时家境贫困。他只身前往北方舞蹈学校,饱受沙漠风沙之苦,被世人轻视。直到人到中年,妻儿分开,他孤身一人,两手空空,最后在歌舞厅打工谋生……在中国度过了大半生后,他回到了中国。和父母一起去了美国。
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还是很长的,作者从20世纪40年代、1950年代写到现在。浩瀚的时间长河承载着不同背景的普通人的悲剧和喜剧。除了主人公小瑟之外,小说还呈现了许多漂浮在上海和时代的普通人,比如柯柯、阿路头、黑三、阿果、“埃塞俄比亚”、“啧啧”等。 Se身边的女人各自的生活都有着自己的缺陷,她们都是城市里失意的人。
虽然王安忆在《长恨歌》之后出版的多部作品中继续写上海,但只有《儿女录》让读者再次感受到作者在《长恨歌》中写上海。 “上海小姐王琪瑶一直怀恨在心,小瑟老叔叔又在风云中翩翩起舞了。”王安忆再次面对城市的皱纹。两部小说串联起来,呈现了上海几十年来的沧桑,探讨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上海的表情和性格。 ,气质。
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批评家戴耀钦以《城市的秘密》为题探讨了《儿童编年史》的创作。文章称,王安忆将人物和时间安排得恰到好处,绕过了对重大事件的详细描述,聚焦于人物本身,细腻地捕捉和揭示了各行各业人们外在情感与内心叙事的撕裂或统一。 。小说标题中的“风云”并不是依靠突发事件和突变,而是会影响风暴的兴衰。

小瑟:黄金世界的局外人
”声音发出缓慢的舞曲,人们陆续上台,缓缓摇曳。就这样,老法师垂下双手,半闭着眼睛……他几乎没有动弹,但全场观众都跟着他的动作。灯光的节奏减慢了,所以我们仔细看他至少有185厘米,身材高了三厘米。而且修长,托起一张脸,悬在空中,不仅因为颜色洁白,还因为立体感,有一种空间感,开着光,飘浮的尘埃不停地移动、转动。倒过来,然后再次战斗,回到原来的位置,这也是可怕的。”
在王安忆的笔下,主角出现在小说的开头,在缓慢的音乐和昏暗的灯光下。 《儿童故事》的主角是老人、老法师、舞者小瑟。故事一开始,这是一个有些神秘的人物。他梦幻般的舞蹈是个谜,他的出生年月是个谜,他的身世是个谜,他的履历是个谜,他的长相是个谜,无论老少,他的姿势是个谜,他的体型是个谜是一个谜。婚姻是一个谜中的一个谜。 “单身生活直接跳到离婚。一会儿有孩子,一会儿就没有了。就像进了道门,没有动作,什么都没有。”这样,小说就散发出强烈的疏离感和孤独感。
当然,随着小说情节的逐渐展开,小瑟的人生观也逐渐清晰起来。小瑟就像一个在舞台上不断旋转的舞者。他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他只是不停地转圈跳舞。身边的亲人不断离开,走出了他的生活:父亲去了西北,缺席了他的成长;父亲去了西北,缺席了他的成长;父亲去了西北,缺席了他的成长。在他的“精神出轨”后,他的妻子离开了他,带着两个孩子去了香港。小瑟意外地在与另外两个女人黑三和阿露头的交往中获得了人生的启迪和温暖。可惜的是,黑三“方正要踩下去,却又停住了,滑了过去,又回到了水平线上”。即便如此,萧瑟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孤独。事实上,他只是金尘世界的一个局外人。
写一座城市,当然离不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人与城市、人与时代相互嵌入、互为镜像。 《长恨歌》中王琦瑶的命运与上海这座城市纠缠在一起,《孩子们的故事》中的小瑟也是如此。不过,小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用自己的一生来展现上海的时代变迁,是作家的另一种视角。
评论家季宏伟在《儿女录:以史为镜、以人为像、以舞蹈为照片》一文中对小瑟的身份进行了界定:本质上,“老夫子”是一个有着“乌托邦”的人精神。追求,悲伤一个宿命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在舞蹈世界里生活、跳舞的美丽青年;一个对现实生活无知且不可靠的老人;一个单纯、直率、无知的孩子,从未在时代的风雨中长大。
王安忆通过主角的口感叹:“他的一生都在漂浮中度过。漂浮的幸福与不幸,漂浮的爱情与无情,漂浮的爱情与禁欲。”
小说最后,阿果带着阿路头去看守所接小瑟时说:四面八方都是红绿灯,生活也是如此。到处都有生命。阿果深知这一点,但萧瑟一生却从未明白过。

还是典型的王安忆风格
很多读者读完《儿童编年史》这本书后感觉,这仍然是非常典型的王安忆,书中的每句话都散发着读者熟悉的王安忆的光环。
我们先来看看这部小说的称呼方式。在写作中,小说的主人公在第三人称和“瑟”、“小瑟”、“老法师”、“叔叔”之间自由切换。当阿果出现或与家人在一起时,“老爷子”的绰号就变成了“小瑟”;当他和学生或同事在一起时,昵称是“Se”;当他和阿路头、李大麦在一起时,个人称呼就变成了“叔叔爷爷”和他。这或许是王安忆在写这部小说时的浅薄尝试。当读者深入进入小说文本时,标题的改变不会造成阅读困难,反而可以通过标题更深入地了解主人公当时的处境。
有学者认为,文学作品的审美风格首先体现在其语言特征上。本书的语言也是王安忆近年来一贯的简单、直白但富有节奏感的风格,句型也多为简单的短句。例如,王安忆在中篇小说《结语》中描写上海的一位老先生:“人就是这样,当他们放弃了挣扎,就有了一种风采。那个老人,穿着‘耐克’牌拉链运动衫。”衬着一头银发,“辉煌。”描述细致,简单直白,没有太多的修饰,类似的句式在《童子实录》中还有很多。 “用稀疏齿梳子拔下几缕前额头发,喷点发胶固定,然后整齐地散开。不要有太多破烂的风的象征。如果太多的话,那就真的是‘破烂不堪’了。谁让他是个老法师呢?他经历了多少年?时代精神终于达到真谛。”简洁的文字更能体现老上海男人的魅力。
作家王威廉说:“小说家在写作时远远大于日常的自我,他能够在叙述中俯瞰各种生活,详细地呈现世界。”它与之前的其他作品非常相似。王安忆的《孩子的故事》也是如此,这是一个经历过人生沧桑的人回望过往的叙事视角。黄浦江边、夜店、沙龙、西洋镜、炸栗子、炸包子、国标舞、现代舞、吉丽雅、阿路头、八卦、弄堂里的麻将桌……作者将这些浓郁的上海元素在叙事中展开然后悄然撤回。她的叙述语境耐心平静,节奏缓慢,是一种充满琐碎、烟火、家常对话的海派回忆录风格。
对于这本书中出现过的人物,王安忆的老读者也会有一点重读旧作的感觉。很多角色都能在过去的作品中找到相似的角色。事实上,正如有读者所说,每一个普通的上海人都可能成为王安忆小说中的人物。
作家叶兆言曾经说过,写得好的女作家很多,但真正越写越好的并不多。然而王安忆却是那种越写越好的女作家。几十年后,王安忆延续了一贯的创作风格和主题,不断探索社会变迁和人物命运。从王琪瑶到小瑟,我们也可以从王安忆的笔下读到沧桑却迷人的上海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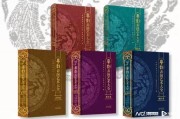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