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的战争:相对论如何征服世界——科学与人文的伟大史诗
相对论大家都知道,但很少有人知道,相对论的提出和验证超越了战争和民族主义的藩篱,结合了两位敌对国家科学家的努力,形成了国际科学共识的基石。
《爱因斯坦的战争:相对论如何征服世界》是一部扣人心弦的人文科学史。它不仅展现了相对论征服世界的历史,也呈现了充满隔阂和敌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个人经历。身处敌对国家的爱因斯坦和爱丁顿是如何付出非凡的努力,克服难以想象的艰辛,使相对论成为现代物理学的基础理论。马修·斯坦利的著作是一部关于科学理性和好奇心如何战胜偏见和民族主义的史诗。这也是对当代科学精神和国际合作的赞歌。

《爱因斯坦的战争:相对论如何征服世界》,
[美国]马修·斯坦利
作者,孙天译,译林出版社出版
>>正文选读: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科学世界
“谢谢你,我已经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爱因斯坦家族热衷于尝试新事物。雅各布和赫尔曼兄弟经营着一家小公司,专注于当时最前沿的创新:电气化。他们在德国南部的大街小巷点亮了电灯,成为该国19世纪末最难以想象的进步之一。 1871年,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取得伟大胜利,随后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因此,此时的德国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统一前的25个公国和王国现已转变为世界级帝国,拥有庞大的军队、快速增长的国民经济以及引领整个欧洲大陆发展的学术和文化机构。这样的德国似乎就是“现代性”的最好例证。 1878年马克·吐温访问德国,他写道:“这真是一个天堂。人们穿着那么整齐,面孔那么友好,充满着那么安静的满足。这里是那么繁荣,有真正的自由。”还有一流的政府。我很高兴,因为我不对这一切负责,我只是来这里享受它。”
马克·吐温访问德国一年后,赫尔曼的妻子波琳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阿尔伯特。当时,他们一家住在多瑙河畔的一座小城市乌尔姆(这里的市铭是“乌尔姆的每个人都是数学家”)。不久之后,爱因斯坦一家从乌尔姆搬到了德国南部大都市慕尼黑。小时候,阿尔伯特直到很晚才说话。他习惯于先对自己重复自己想说的话,确保其正确后再说出来。他的脾气也是出了名的,整张脸都黄了,鼻尖也白了。据艾伯特的姐姐说,有一次他的哥哥生气了,用锄头打她的头。
爱因斯坦一家是犹太人,但几乎完全是世俗的。德意志帝国对犹太人几乎没有任何法律限制,但许多反犹太传统仍然存在。像大多数同化主义家庭一样,爱因斯坦家族深深地融入了德国的世俗文化。赫尔曼晚上会给孩子们大声朗读席勒和海涅的作品。波琳是一位技艺精湛的钢琴家,希望阿尔伯特成为她的音乐伙伴,所以她在他六岁时开始教他小提琴。此时的小男孩阿尔伯特讨厌这种机械重复的训练,所以他才无奈地学习了音乐,这似乎是未来的标志。直到多年后,当阿尔伯特发现自己对莫扎特奏鸣曲的热情时,他才开始全职学习小提琴。多年后他回忆道:“我绝对相信,爱是比责任更好的老师,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然而,对他来说不幸的是,当时的德国教育强调责任而不是爱。阿尔伯特就读于离家最近的学校,那是一所天主教学校。学校纪律严明,崇尚军国主义。艾伯特不喜欢一直被告知该做什么,所以他几乎与所有老师作对。他曾经用椅子打导师,总喜欢称呼老师为“你”而不是“你”,这很烦人。根据爱因斯坦的家庭故事,一位老师曾严厉斥责艾伯特说:“即使你只是出现在这里,你已经被全班同学不尊重了。”但这句话对阿尔伯特没有任何影响。有什么影响呢。
阿尔伯特几乎没有朋友,而且从小就非常独立(四岁时他就可以独自走在慕尼黑最繁忙的街道上)。他最喜欢的游戏是用纸牌盖房子。与流行的故事相反,艾伯特的成绩并不差。学校一直强调古典语言的学习,这不符合艾伯特的口味。因此,阿尔伯特的继续教育大部分来自家庭。年迈的阿尔伯特曾经回忆起点燃他对科学热爱的那一刻。在他四五岁的时候,喜欢小东西的父亲送给他一个指南针作为礼物。指南针上的指针始终指向北方。这个简单的现象让年轻的阿尔伯特着迷。艾伯特对现象背后始终保持不变且从未出错的无形力量着迷。这些是什么?类似的事情还有吗?可以理解他们吗?如果是这样,应该怎么办?
十一岁时,阿尔伯特开始严格遵守犹太洁食规则(他的家人既没有要求也没有支持),但这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很快,到了第二年,阿尔伯特发现了自己脑海中的“神圣几何小书”。爱因斯坦夫妇经常邀请一位名叫马克斯·塔尔穆德的贫穷医科学生到他们家吃晚饭。塔木德和雅各布叔叔给阿尔伯特带来了有关科普和数学的书籍。在阿尔伯特看来,正是这些书促使他开始自由思考。这些书中,最关键的几何内容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它一直是欧洲两千多年来数学教育的基础。全书从几个不容置疑的前提(如两点确定一条直线)出发,通过缜密而有力的论证,发展出多个复杂的推论(如毕达哥拉斯定理)。这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让艾伯特震惊不已。艾伯特曾这样形容这种感觉:“这些结论的证据是如此确定,不容质疑。这种清晰性和确定性给我留下了难以形容的印象。”这成为阿尔伯特思考自然世界的一个模型:从一个清晰而有力的想法出发,通过演绎得出结论,在演绎过程中你也可能得到一些有用的想法。
对于阿尔伯特来说,尤为重要的是,这本书中的知识似乎超越了人类个体,是深刻而超然的真理。因此,数学和科学成为阿尔伯特摆脱人与人之间琐事束缚的一种方式。十几岁的时候,阿尔伯特就宣布自己将来要成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正是因为理论物理学可以使他独立,独立于社会和习俗,独立于传统和权威。他还承认,他缺乏实用主义,这意味着理论物理学比应用物理学更适合他。
虽然学校制度僵化,但爱因斯坦完全愿意坚持下去,以达到学校的期望,但他对毕业后将面临的未来深感恐惧。所有德国男子毕业后都必须参军,爱因斯坦也不例外。学校生活已经够糟糕的了,他不认为自己还能过上踏实的军旅生活。于是,1894年,他稍微动了一下脑筋,找到了自己的一位世交,说服他给自己开了一份诊断证明,上面写着自己患有“极度神经衰弱”。在19世纪,这种情况极为常见,其特点是脑力过度消耗和神经系统极度疲劳。爱因斯坦利用这一诊断来阻止自己提前毕业和辍学。后来,他甚至更进一步,正式放弃了德国国籍。如此一来,德意志帝国就再也无法约束他了。
果然,面对突然没有文凭、没有工作的儿子,爱因斯坦一家一点也不高兴。幸运的是,有一所优秀的学校不要求学生在入学前获得高中文凭: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艾伯特说服家人让他通过自学参加这所学校的入学考试。第一年他没能通过考试,但经过一年的准备,他成功被录取了。他发现瑞士(尤其是苏黎世)是一个比慕尼黑更加自由的地方,他在这个新环境中茁壮成长。
然而,爱因斯坦的学习习惯并没有明显改善。如果他觉得某堂课无趣,他就会经常逃课。尽管许多中欧最好的数学家都在学校任教,其中包括赫尔曼·明科夫斯基(Hermann Minkowski),他将爱因斯坦描述为“一只懒狗”,但学校经常开设数学课。幸运的是,爱因斯坦与马塞尔·格罗斯曼成为了朋友,马塞尔·格罗斯曼是一位勤奋做笔记的数学学生。爱因斯坦会研究格罗斯曼的笔记,然后参加考试,尽管他考试成绩很好,但他会因不认真对待学习而受到学校的正式谴责。后来,爱因斯坦回忆起这段人生时,对格罗斯曼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说:“我什至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这些笔记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即使在物理课上,爱因斯坦也几乎没有集中注意力。这些物理课程往往侧重于成熟的主流物理学领域,避免了电动力学和热学方面尚未确定但令人兴奋的新研究。这与今天的科学教育没有太大不同。此类课程并不是为了训练学生进行新的科学研究,而是为了确保他们掌握他们已经知道的知识。因此,学生必须一个又一个地背概念,一个又一个地解决典型习题,一个又一个地重现经典实验。爱因斯坦和朋友们只能自发地阅读当代物理学的最新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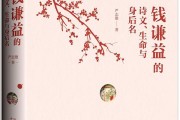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