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初见时出版,收录史苇湘、欧阳琳、史敦宇一家两代三人 112 幅壁画复原作品
石敦玉的新书《初见敦煌》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收录了石维祥、欧阳林、石敦玉家族两代人的壁画修复作品112幅。书中记载的作品涵盖了敦煌壁画中最具艺术和人文价值的六大题材:故事画、经画、飞乐舞、世俗生活、供养人肖像、敦煌遗画,特别是遗失在海外的遗画。敦煌经洞。 19幅修复的画作。

《初见敦煌》
对于石伟祥和欧阳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范金石曾回忆道:“石伟祥先生是我了解和学习敦煌石窟艺术的入门老师,他对每一个石窟、每幅壁画都了如指掌,他是家族的瑰宝。”他们二人将自己的青春和热情奉献给了敦煌艺术的研究。”
“1943年,张大千在成都举办‘福临敦煌壁画’展。当时,我的父母是四川成都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在老师的推荐下,去志愿参加大千先生的画展。”展览期间,学生们被敦煌艺术所吸引,告诉我的父亲,你想成为一名中国画家,就必须去莫高窟,去临摹、去体验。莫高窟你就会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多么优秀,这么悠久的历史是多么珍贵,从那时起,我的父亲就对它痴迷了,第二年就想去敦煌。敦煌艺术研究院成立,常书鸿先生正在为莫高窟的保护研究缺乏人手,他向张大千先生提到了人手不足的问题。推荐了一批像我父母这样的学生,我妈妈欧阳琳和她的几个同学一毕业就去了敦煌。我的父亲石伟祥参加了青年探险。军队推迟了学业,晚了一年才抵达伦敦。 1947年,我的母亲和其他人到达伦敦。当时,段文杰先生亲自驾着牛车来接他们。当时,女同学们都穿着时髦的旗袍。镇上的人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纷纷追着车去看这群充满激情的艺术年轻人。它给小镇带来了新的面貌,也为莫高窟的保护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石敦玉在书中回忆道。

段文杰先生驾驶马车迎接新会员
在敦煌的日子物质上极其艰苦,精神上却极其丰富。 “刚到莫高窟时,父母就迫不及待地跟着常书鸿先生进洞学习临摹。父亲说,这是‘一见钟情’。刚进洞时,他就被那古老而宏伟的壁画和彩塑所震撼,我们恨不得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从温暖湿润的四川盆地到沙沙荒漠的边疆。不可避免地生活中遇到各种困难,水是生命保障最基本的资源,但据我父母说,刚来敦煌生活时,水对于他们爱喝茶来说成了一个大问题。没想到这里的水不能用来泡茶,因为敦煌的水源是在祁连山,山上的雪水本来就很好,但是在旅行的时候却流入了莫高窟的小沟里。 ,你必须经过一个大面积的白花盐碱地,水质变得很硬,你很不习惯。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我不敢穿黑色的衣服,因为大家都在河里洗衣服,黑色的衣服晒干后会有白色的污渍。这是因为水中的盐分太重了。生活中,连喝水都困难,更不用说其他的了。”

石伟祥正在洞壁上临摹
由于父母工作忙,石敦玉两三岁的时候,刚学会走路就自己跑进山洞。 “常书鸿先生怕我打扰他们画画,就把大皮靴在湿沙里擦了擦,把表面擦得光滑,又拿起一根榆树枝给我当画笔,对我说,你你看我和你爸画汉代古桥,你来试试看你能画多少,他们画完后,发现我的“作品”也很像,洞里的色彩和图像也扎根了。我的心,从一棵榆树开始。江滩枝桠,一画终生。”石敦玉说:“在父母的影响下,我一直沉浸在敦煌壁画的修复中。我当了几十年的美术老师,培养了很多对敦煌艺术感兴趣的学生。我埋头在敦煌壁画的门前。”莫高窟,我已经七十多岁了,但敦煌艺术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却是永无止境的事业,让更多的人欣赏和了解敦煌,这就是修复壁画的美育意义之一。”

石敦玉为修复后的画作上色
五十多年来,石敦玉专注于壁画修复。她的修复图是基于她父亲留下的大量第一手线条图,并将它们复制在洞穴的墙壁上。 《敦煌初见》中的修复图片,都经历了两三年乃至几十年的复杂工作。其中,巨幅原版修复画《西方净土变》目前正在敦煌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
“这些年虽然我生活在兰州、北京、上海等地,但敦煌一直是我一直梦想的地方。敦煌的水和土壤养育了我,莫高窟的文化氛围塑造了我。”那些宏伟的壁画和绘画,那些生动神奇的石窟故事将永远留在我的画布上,成为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我一直相信我的家在敦煌。”石敦玉说:“敦煌是一本读不完的书,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是我们祖先永无休止的事业。耐得住寂寞、扶贫的莫高精神至今仍将延续,每一代人会做出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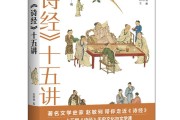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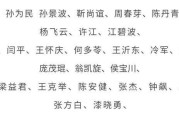
文章评论